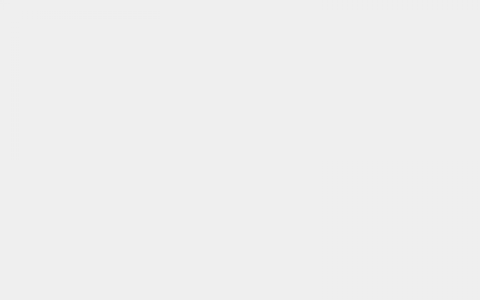天一黑,我就不敢到屋外去了。如果让我出门拿个东西,哪怕就在院子里,我都要在门口酝酿半天,提着气,硬着头皮,推开门的一瞬间,就开始飞奔,还会“啦啦啦”地喊两声给自己壮胆。
跑着去,跑着回。
哪怕那个东西就在推开门的两米处。我也是同样一通操作。
每当我这么做,我妈都用嫌弃的眼光看着我,笑话我:“胆子怎么这么小,以后成不了大器。”
这其实不怪我,谁让我小时候我妈总是吓唬我。她告诉我,天黑了不要乱跑,要马上回家,外面有“鬼”。
你看,父母有时候就是这么“双标”。他们把吓唬孩子的那部分,和孩子被吓唬后形成的结果,完全分裂开看。为了让孩子“不乱跑”,吓唬孩子有鬼;孩子信以为真,结果别说乱跑,连出门都困难了,他们又笑话孩子胆小。
2.
小孩子怕“鬼”,其实可以理解。
皮亚杰的“儿童泛灵论”认为,在“前运算阶段”,也就是2-7岁,儿童无法区分什么物体是有生命的,什么物体是没有生命的,而是会把自己的意识和意向推向所有的物体,认为,所有物体都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意识、有情感的。而且,在这个时期,儿童处于对外界事物逐渐积累认知的阶段,父母是儿童认识外界事物重要的通道之一,在孩子对未知既恐惧又好奇的时候,父母的引导就显得极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如果吓唬孩子外面有“鬼”,孩子会深信不疑。
怕“鬼”,是一种人对未知事物本能的恐惧。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拟人化为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史,人类在原始时期,当对世界的认知还没有这么发达时,出于防御的机制,我们倾向于产生恐惧的情感。恐惧,可以让我们规避危险,保护我们的安全,让物种得以繁衍和壮大。于是,对于未知的神秘力量,人产生了本能的两种解释:一种是神,那是好的力量,要崇拜起来;一种是鬼,那是坏的力量。这沉淀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之中。
小孩子在受到人类集体潜意识以及个体发展中周边环境的影响,怕“鬼”,就不难理解。
曾经有读者在后台提问:家里小孩子很怕“鬼”,怎么办?
上面的解释,可能能缓解这位读者的一部分焦虑。小孩子怕鬼,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作为父母,我们不用过于担心,明确告诉孩子,我会陪伴着你,这很重要。
除此之外,做为家长,我们在担心孩子并问出“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先觉察一下自己:为何这么焦虑?
3.
儿时怕鬼不难理解,可是,长大后,很多成年人还是怕“鬼”。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怕“鬼”,但是又似乎有点羞于承认。比如,我的一位朋友,晚上一定要开灯睡觉。这个习惯从他毕业后单独生活,就一直存在,就是因为害怕。
有一次,我问他:“你怕什么?”刚问完,他一个一米八的大男人,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跟你说你别笑话我,其实挺幼稚的,我怕‘鬼’。”说完,还不忘再补充两句:“我是无神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可是,我就是害怕。”一边说着一边双手一摊,以示“对于这种情感上的恐惧,是自己理性不能触及的地方”,自己无能为力。
因为怕“鬼”,他在刚毕业的时候,甚至一定要和别人合租,而不能自己一个人住。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描述过一个意象:每当她老公出差,她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当她晚上睡觉,在闭眼之后,她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鬼”。这个“鬼”从黑暗的远处,由远而近,最后无比狰狞地贴近她眼前,极其恐怖。
4.
怕“鬼”,到底是在怕什么呢?我们不妨一起来感受一下。
开灯睡觉的习惯,我自己以前也有。
想来也是,小时候被父母吓唬得在黑夜中只能狂奔的我,长大后似乎想不怕“鬼”也难。
感受一下我自己要开着灯睡觉的原因,这个心理活动似乎是这样的:我要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能逃脱我的“法眼”。似乎,只要我提高警惕,盯住了周围的一切,那么,我就控制住了外在的环境。外在环境尽在我的掌控中,“鬼”就不会出来害我。
所以,我们怕“鬼”,似乎是因为我们对一个事实坚定不移地相信:外面一定有一个“鬼”,总是伺机要谋害我。
也就是说,外面的世界,是坏的。
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小的时候,我是跟随父母在家乡以外的城市长大的,父母一直认为,我们一家人受到严重的、无处不在的地域歧视。地域歧视的情况,在当年确实存在。然而,因为我的父母本身的性格和心理状态,他们严重地放大了这种影响。
他们给我灌输的理念是:我们作为“外地人”,是受到所有人歧视的。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很坏。跟周围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要不然就会被欺负。而且,在我的记忆中,父母的性格似乎也很软,回家总是说一些“因为自己的善良,对方的无情”,结果被欺负的事情。
所以,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很胆小,我的生命一点都不舒展,皱皱巴巴的,顾虑重重。我害怕很多东西。尤其典型的,就是怕“鬼”。怕鬼,除了因为父母的吓唬,似乎也成了这样的一种隐喻。
5.
怕鬼,还可能是:内在的黑洞,投射到了外在鬼的身上。
外面的鬼,里面的自己。
当外面的世界是坏的,我们就会收回对外面世界的信任,只能依赖自己。在我们收回对外面世界的信任的时候,我们一并收回的,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当我们把这种敌意、防备和恐惧安放到自己身上,我们的心理,就会出现很多的黑洞。而这种黑洞又会投射到外界,从而来印证:外面的世界就是坏的。
比如,鬼可能是自身“攻击性”的投射。
既然外面的世界是坏的,随时可能伤害自己。我们很可能就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对这个恶意满满的世界有很多的攻击性,但是,又不敢表达,因为,如果自己一旦表达出攻击性,这个“坏”的世界一定会回击我们,我们就会遭到“报复”。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像“衔尾蛇”一样的死循环:因为世界坏,我们产生了攻击性,但是一旦攻击出去,我们又会被报复,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咽下”我们的攻击性。但是,“攻击性”做为人的根本动力之一,岂是说咽就能咽下的?攻击性在我们的身体中蠢蠢欲动,而且,总会在某些时候冒出来,连我们自己都吓一跳。
我的一位来访者,有强迫倾向。她怕“鬼”。而她所怕的“鬼”,就是她自己的攻击性。
来访者家里条件不好,一直都被父母忽视。因为这样的经历,她一直对家人有“攻击性”,所以,她脾气曾经非常暴躁。但是,在她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她和父亲大吵一架之后,她强行挂了父亲电话,就在当天,父亲因为发生意外去世了。虽然理性上她认为很荒谬,但是,这给她一种坚定不移的错觉:似乎是她的攻击性“杀死”了父亲。从此以后,她性格大变,跟家人看起来相处变得非常融洽,但是同时变得很胆小,开始“怕鬼”。
这是因为,她开始压抑自己的攻击性,她认为,她的攻击性就像魔鬼一样。为了压抑自己的攻击性,她开始有一些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行为是为了来抵消她的焦虑思维。她的焦虑思维是什么呢?每当自己似乎要发脾气的时候,她就觉得四周顿时变得非常可怕,似乎有一个无恶不作的“鬼”出现,会伤害她的家人。而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举动来抵消自己冒出来的这种像魔鬼一样的“攻击性”:比如水龙头一定要关几次,洗澡一定要洗多少下,走路一定要走到路砖的缝隙上等等。
6.
怎么破?
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方面去做:
第一,收获一个好的外界。
我们当然不能被父母重养一遍,我们可以做的是:看到好的关系、关系中的爱以及关系中的人。这种方法,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重养一遍”。
比如,我在小时候,常年被父母灌输的“外面都很坏”的感觉,曾经对我影响深远。在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很孤立,不合群,似乎总是非常警惕,总觉得自己稍不留意,就会被人欺负。这种情况之所以会慢慢好转,那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真的伤害到我,从朋友,到老师,再到两性亲密关系,以及工作中的老板,其中重要的一些人,他们都对我表达了足够的抱持、支持、理解和善意。这些爱,滋养了我,也改变了我,这对我后来的转变,有直接的作用。
第二,接纳自己的黑洞。
心里压抑的恐惧、攻击、愤怒等等情绪,我们常常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去表达,从而被我们压抑。因此,一旦它出现,我们自己也吓一大跳。而这些东西的出现,不过是要求被看到,被承认,被接纳。你知道,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的出现,是为了“杀死”你。他们的出现,不过都是一种提醒。
外面的世界有好有坏,别人有好有坏,我们自己也有好有坏。那个鬼,也许一直都会在。如果在,就欢迎它,那个被所有人唾弃、阴暗的、不被接纳和理解的鬼。
第三,寻求帮助。
有些孩子是因为幼时不小心受恐怖电影、黑暗场所、鬼屋等恐怖场景或者恐怖的梦境影响,受到惊吓,在潜意识中留下恐惧的记忆。因为这样的情况造成的怕鬼或怕黑现象可以通过催眠或其他心理治疗方法予以解决。
呼吸与时间一起,将我粘在“年画”的星光里。
我人光一体的,在扭曲的空间,构建着眩晕的梦。身体在升温的晨光中隐听到了光明的呐喊。渐渐觉悟的身心,将还残留并躲藏在残梦里的阴暗,驱赶出身体。出梦,就被妻语言的快门,定格在觉醒的晨光中。你心里发慌,现在,就去看医生去。对,就是现在,查一下,我们也好放心过年。
我偶尔心里发慌,从疫情再起就有了。我已忽略此事,是我已用我自己意识的力量,将身体的浊气排出。现在妻提起,也就不说,随从而去了。去医院的路上,阳光洒洗着我寒冷的身体。阳光温暖着,一改昨夜脸上留下的倦意情绪。可坐等医生1个多小时,我还是胡思乱想了60分钟。医生很简单地询问病情后,就将我交给了机器。拍胸片,心电图,抽血化验,一系列检查之后,再找医生复看。医生看了我全部的检查资料后说,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可能有早搏现象,回去注意休息。我疑惑地问,这就结束了,也不用吃药。你自己想开药,就给你开一点中成药。我说,前一阵失眠?加强锻炼就好了。去交钱吧!走出门诊,去打医保卡,卡被卡住了,取不出来。只好,等下午上班的工作人员来。我正在与人交涉,又一女声叫,我的医保卡被卡住了。我分别打了医院的许多电话,都没有人接。保安说,打市长值班电话。我笑笑,你给我电话号码。没有办法,就地过年还没有开始,我们就被迫就地午餐了。等再取回医保卡,回家已是下午了。
听医生的,背着运动包去锻炼。一出门就遇到出小区去买坚果的敬老院院长。同路走,话题都是疫情与过年。我问院里就地过年的人多吗?回家过年的就2人。现在共45位老人,还有一位百岁老人的家人问,百岁是家里过好,还是敬老院过好。百岁人少,还家里过温情些。听了劝说,过两天这位到百岁的老人,就被接回家过年。哎,搞敬老院,责任心大,干了十八年了,有人接我就不干了。我说,这是做善事,看你过的,快70的女人,看上去也就50来岁。院长问我,你哥不回来过年了?家人都响应号召,就地过年了。以往这个时候是最忙,哪里像现在,还能去打球。什么定酒店,返程票,家人、同学、朋友协商请客时间。哎呀,买酒就得好几箱。还要选一 旅游 线路。情况突然变了,省钱省时还省力了,可这人还不适应了。说着话, 体育 馆到了。我从这转了,打球的地方到了,再见了!
入乒乓球馆,泡好茶,正做准备换运动服时,老冯走进门就说,来迟了,今天,打新冠疫苗第二针。那你还来打球?一点反应都没有,凌老师看,连针眼都看不见,冯一边说,一边就露出打针的地方给我们看。医生是说不能下水,那我不洗澡就是了,没有那么多讲究,注意就行了。就坐在我对面的小马说,我女儿也打了新冠疫苗。毕教练接上话,许多人怕有后遗症,都借口不打,年轻的小护士就以怀孕为借口。话题都围绕着疫情,我就问坐在我身边的小朱,你女儿不到美国上学去了?现在人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还有一学期,就毕业了。说起来好笑,学费还是交到美国学校去,人在上海音乐学院上课。坐在我左边的汪明也说,我儿子也因疫情,从澳大利亚回国了,现在就在铜陵工作,也不去澳大利亚了。你不是说,儿子在澳大利亚分房子吗?是分房子,但不安全,也就放弃了。我说,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生活方式,逼着我们改变。谁人不怕这疫情?汪明立马脸都变了色的说,我真怕!畏惧感的他,还做着相应的动作。正说着话,一个陌生人走进乒乓球馆。毕教练问,哪里的,蚌埠。外地人要看 健康 码。凌老师,来打球。冯在5号桌边叫。我拿起乒乓球拍,跑过去。
晚上,侄儿小鸣打妻电话问,姨夫看医生怎么说。小鸣是我们的医疗指南,看医生之前,妻咨询过他。妻说了看医生的情况与检查的数据。小鸟哈哈大笑,姨夫的身体比我好许多。那开的药,就叫自我安慰药。或许是姨夫感冒了,自己不知道,引起了一点身体不适反应。也如医生说的,注意休息。小鸣侄儿活血通络的话语,化解了我的焦虑,更使我的心情舒畅起来。
妻问小鸣,你儿在合肥学习现在怎样,复读考上大学了,我们庆贺一下。别提他了,怎么了?妻疑惑起来。前几天,学校学生食堂集体食物中毒了。啊!人怎样?不要紧张,现在没事了。我连夜赶去处理。哎呦,怎么没听你说。当时,我们都吓晕了,就想着早点去合肥,哪里还想到别的什么。妻说,非常时期,要保护好自己与家人,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好,没有事就好,我挂电话了。
年,刮起的味蕾波浪,将邻居家炸圆子的气味飘到我的空间。心态安静下来的我,就在这年味忽升忽飘的环境里,油香又热乎地恢复写中断的日记。思维随香转换到文字里,昨天还沉重与昏沉的头脑,也就在这年味的飘散里,忽然间渐渐明朗起来。其实,那本来就已生长在心里土地上的文字,是被焦虑笼罩着看不见。现在思想的太阳一照,鲜嫩与可爱的文字,在光亮里显露起来。看,那飞舞在文字里,的小蜜蜂与小蝴蝶,扑闪着逻辑的翅膀,微妙出时间深浅里的花事来。思想的流水声与键盘上的敲击声,在生活的空白处,流淌出一种愉悦来,存在中的我消遣地写上日期。
我还借着指尖的力量,将这沸腾的年香与文字一起,徐徐又缓缓地从拼音的碰撞声里,录入到读书笔记里,没有想到,字里字外的年香与当下时钟滴答地走动,使身体里的年声也在回响。两个维度都在变动的时光里再次告诉,中午就要到了。文学不能当饭吃,身体里的指令,下意识地催拉着我,做午饭的时间去了,应该转场做饭了。
随着年到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在家调整心态的我,心情一天比一天好。防疫情期间,人就一如时间水包裹的千岛湖上的孤岛,只是凭着手机与外界联系。突然,手机响了。电话吓我一跳,我生活的天空,突然飘过来一朵黑云。看着云朵激动起来的我说,好,马上就到。刚穿好外套,手机又响起,疫情期间,医院要有核酸检测才能进,怎么办?我们协商,微信时代,就微信探视吧!我立马微信视屏这位死里逃生住院的同学之后,这同学就发来一段让我读了久久不能平静的短文:xxx你们好:谢谢你们的关心,慰问金暂且留下,心意永留心间。目前,虽说四处骨折,但主体功能不受影响,头部内脏完好无损。谢谢同学、朋友亲友们的挽留,让我重新获得新生。交警通过视频都说是个生还的奇迹。经过26天的治疗,恢复很好,目前,已能下地行走。谢谢你们的关爱与鼓励。我将很快就能和同学们谈笑在酒桌上,游玩在山间田野。再次问好同学们。
我脑海里沉默的往事都被这条信息引发联动起来。文字加回忆,变成我脑海中播放的电影。我与这同学也是发小,曾经一起结伴,从少年的小巷出发;一起欢快地穿过青草地,又乘风破浪到广阔天地;为爱相伴走上青春的十字街头;手牵着手又一起跨越时代的鸿沟,互相鼓励地穿过改革的大街小巷-----都是人生的老运动员了,怎么在年门口等车还发生意外。看来,永远在年龄与变化中行走的人,活在人生的路上,是要处处小心的。
现在,我把这事物沉默的本质引向表述,是眼含着热泪的,人还是故意看着远方飘荡的云的。人生路上40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能如天上的云,说散就风散了。现在我与云的连接与表达,不是要表示什么曼妙,而是要借云,连接上我的 情感 ,也用云连接,表达出我如云朵活泛的想念状态。我说着话,风变幻着云态。我把心的连接与交缠,呈现在遥远又心近的同一个受力点上,再传输出去,我想,我的那位在今年的路口,人被撞飞而住院的同学,定会从文字飘来的云朵里,得到云生的力量。将文送入云端后,我不敢再演绎与延伸,这同学当时被撞的画面了。
年,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回家的身躯与光影,混合成的传统风俗画。这融入到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与血液里的年声,从出生起,就成了我们自己身上的乡土元素。又随生活年复一年地长出新枝,发出新绿又开出时代的新花来。你听,那浩浩荡荡又滚滚向前的时间之水,正汇聚着时间深浅的每一滴水声,时光荏苒地彼此碰撞着浪花,向上释放着激情。一滴水融入一滴水的,衍生绽放出“远看草色近却无”的早春年画来。
思维在提醒我,年前,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记录好日记,我立马联系租弟家的住户,将6个月的房租,用微信打给小弟。在海南陪女儿读书的小弟,将他家的房事交我打理。我想起,到上海之前,拿回家的《汗淋淋走过这些词》,凌越今年出版的第三本新书还没有读。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凌越的这本书,语言的密度与文学的强度,都大于从前。我对于他在电脑闪烁的光标之后出现的文字,充满了期待。我打量着书的封面,就如我们兄弟对坐互相打量一样,然后,闻着嗅着,茶从玻璃里升上的香味,再浅口小抿着茶,就如与他谈心一样地翻读起这本书来。
妻子,在年水街的各色门里穿梭,人如春燕衔泥,一天天从街上买回一些东西,置办着年货。而24节气的词汇随风而来,也随风而去。说话间,立春就到来。
立春这天,我们仪式感地脱掉冬装,换洗床单,洗澡,开窗,让春风吹进来,春光照进来。与妻一起做着立春的菜肴,仪式感地油炸着藕圆子,吃着春卷与散发的韭菜,喝着象征的两白,莲子、银耳冰糖熬的汤,一边咀嚼着岁月的味道,一边看着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嘴里咀嚼着自己做的糖果,眼睛里闪过春春的倩影,身体与味蕾一起,音乐起爱的味道。春的滋味,自嘴里往心里流动,而内心记忆的过往,与双重生活叠加在一起的味道,缠绕在一起,重重叠叠的细微着感觉的我们。
春天,生活的流水有潺潺之声了,再细听,每一滴生活水里,都有静好的春光之妙了。立春这天,微信群里传出,《世界文学》有直播活动。我早想闻闻这2021年《世界文学》第一期早春文字的味道了。也想抢先品一品,世界不同语系春天里语言的新涟漪了。也想从新的语系里,寻找发现新的语言组合元素,借他山之石,建自己的文字“城堡”。我私下也想见一见,正在文字春天里耕耘在《世界文学》里的这帮人,品尝编辑们用心烹调出得舒心又爽快的文字大餐。通过直播活动的聆听,走进《世界文学》编辑部,也与编辑们聊聊所谓《世界文学》背后的那些事儿。然后,再从期刊文字的丛林里,有趣地去追踪意大利作家佛朗哥·阿米尼奥笔下 “没有面孔”的黑暗 “深渊”;重新认识西班牙女作家伊莲内·巴列霍所说的 “维系 社会 ”、照拂人心的 “看护者”。跟随作家田中禾思考作家在“文学不再打动人心”之后面临的诸多问题。看看魏怡写的《立体的文学》。我想入非非,可是直播时,我急得像热锅上蚂蚁,钻来钻去,就是进不了直播间。没有办法,也只有等期刊到了再读文字了。阅读后,再从微信网站《世界文学》分享会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通古今变化的时间,虽然没有将远方与诗全部惠赠与我,可我还是从滴答的时间流水流声中,收到了“漂流瓶”。打开邮包,文字浮现眼里:《2020中国散文精选》《2020中国年度散文诗》《2020中国年度精短散文》。身体里阅读的力量,发热地唆使我快速进入。脚步一边移动,眼睛就开始扫描起来。眼神立马就进入到,年选系列的世界之中。诗与远方与散文的时态,诱动着我饥渴的心。文字上的心光,映照着我,使我近日应疫情焦虑而板结得脸上也松软得光亮起来。
放下,还原自我。当下被年味文火慢炖,开始与“年”一起酥软又冒着愉悦味道的我,立马想起,2021的期刊一本都没有到。这些文字里的存在,丢失在哪里?打电话问邮局。回答,疫情防控期间,北京与北方来的邮件停运,什么时间开启,等待通知。又是疫情,割裂了我期刊适时的阅读。我真想,突然变成一个医疗战士,上前将这该死的病毒立即杀死,使疫情快点早点结束。
小年,大弟打来问候电话。我说,现在过年的程序一切都简化了,过去祭灶日,还要做糖糕、米粉糖馅团子,现在,我们就象征性,简捷化炸个圆子,就完事了。年味也就这般一年的越来越淡了。大弟笑着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年货不缺什么了吧?我不回铜陵过年了,也就地过年了。然后话锋一转,你们带着我的那么大画在路上,确实不好拿,检查好过吧?我用手机对着他的颤音抽象画《春天的脚步》说,都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了。我喜欢这幅画,是因为这画里画外都有我与兄弟们少年足迹的声音。那油菜花与灼灼桃花,遮蔽与敞明,沉默与言说,颤动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少年的心呢!大弟是在用画笔,重新发现故乡,用色彩讲述我们昨天的故事。这来自生活的色彩与原音,时常吸引着渗透到昨天时间中的我。大弟勇敢 探索 ,创建了新的颤音抽象派,并于近期还创办了《上海市黄浦颤音抽象艺术研究院》。从绘画理论到实践的投入在创新中。承办了许得民书写艺术展《见证虫书》获得圆满成功。我告诉大弟,很喜欢近日画的《生命隧道》,简洁又明朗地讲述了人生色彩的变化。红、黄、蓝变成黑,所以,我以为黑色里,也有我们所说的红、黄、蓝。生活的黑里有白,白里有黑。黑白转换,就是我们的世界。大弟说,电视台说明天要来采访,就不多说了,我也要准备一下。
洗澡,理发,贴上春联,大年三十晚就到了。今年,我们家的这一年中最讲究的一餐好饭——年夜饭,是在我与妻的话语中,就着碎碎念念与远方明亮如诗句孩子们的往事,在煎、烧、炒、炸、蒸的声响与气息里一起完成的。一桌盛满岁月的菜肴,仅凭两双筷子,是挟不起全部年味的。过年,团圆的意念,挤占着年味正浓的空间。自我打量还冒着热气,已成作品的菜肴,内心里虽有一些被掂量过的冷词在往外冒,但图吉利,讨好彩头的我,还是将它们压下去。用另一种绵长的暖语,其乐融融地连接着味蕾初开的心情。
同一纬度上的酒杯刚碰响,远程的外孙就热闹地敬酒。我与妻抱团取暖地放大快乐的画面,再次举杯。并用我的冷幽默,制造着笑声。还自我欣赏的以念台词的语感,艺术着年夜饭的录像。然后,让微信裹着老家的年味,给外孙打去压岁钱。一会我与妻的手机都响了。一看是女婿给我们的压岁钱。我们不收,也就是不点收,24小时后,让“压岁钱”自动转回。过小年时,女儿就说要给我们一个整数的压岁钱,我们坚决不要。因为,孩子读书,用钱的地方很多。这又改时间来了。年味的芳香已入肠胃,意识与肠胃一起蠕动时,味蕾里响起声音。刺激的神经在混合的酒香与菜香里寻找,原来是我的手机。手机屏里,女婿温顺地在喊,爸,妈,我们做下辈的一点孝心,你们都不收,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呀!女儿将头伸进手机画面说,收下,一定要收下。你们不能剥夺我们的孝心!点,立马点!外孙也插进手机的画面在喊,外公阿婆,我也收下你们给的压岁钱了。你们也要收“压岁钱”。被孩子们话,催得心里温暖发热的妻,内心里发出微笑地看着我。女婿又说,过年,不就哄哄热闹吗!爸妈,我们一起祝你们,新年快乐!疫情过了,明年回来过年。干了!
陪读在海南岛的小弟,打来拜年视屏电话,问我怎么还有火光。我说,正在给爸爸妈妈烧“年包”纸钱。这是我们家从过年祭祖,留下的一个过年必办的一件事。过年不忘初心,用烧纸来寄托我们对先人的 情感 。小弟与我互相拜年寒暄后说,他们也正在穿外衣,也准备去烧纸去。并说,都好,我就挂电话了,出门烧纸后,回来看春晚。
春晚,成了中国人守岁必看的节目。我与全国人民一样,一边看春晚,一边卤着茶叶蛋。屏幕内外的香气与年味,使我的味蕾在年香的弥漫里,追忆起逝水年华里与年味关联的许多往事来。文火煨出的茶叶蛋味道才真好。妻子与我一起敲着熟鸡蛋的外壳,一边说,我就喜欢吃小时候,锅洞里瓦罐煨出的肉,那个香,现在一提起都要流口水。柴火饭,文火炖肉还有一些农耕文明的美味,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那些充满着烟火味的 美食 ,也只能是留在舌尖上的记忆了。
春晚的音乐,已从我的舌尖上开始。从中国文化根脉上取火,用年味与春色装台的春晚,点亮了我的味蕾与守岁的情趣。我也与千万中国人一样,聚集在时代运行的站台与看台上,一边总结着过去又展望未来的,人与电视互相渗透在时间里。一边看着大屏幕,又一边期盼新年时光车的到来。
年,是我们精神的故乡。她承载着我们年轮里的记忆与乡愁,也年复一年滋养着精神之根。年,还是我们生活的加油站。无论你走多远,只要回一次家过年,浑身就添加了力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有年的印记,无论你寻找童年还是中年的样态,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品咂出花样的年华。
庚子年的时间水,从我身上湍急流过,留下了这庚子年记忆的擦痕。我将这些经历着的逍遥与存活里的自然,与量子纠缠不同方向的力连接起来,就围合成了我文字叙述能量的空间。
作者简介:凌代琼,安徽铜陵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多次获全国各类散文奖。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40多万字。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