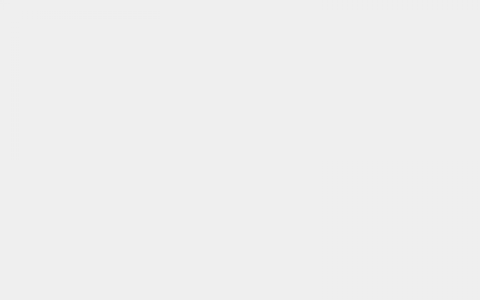2.母婴传染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可通过胎盘而使胎儿感染艾滋病病毒,也可在胎儿分娩时,经产道而传染上艾滋病病毒,部分婴儿也可由乳汁而传染上艾滋病病毒。
3. 血源传染 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浆或血制品,静脉药瘾者共用污染艾滋病病毒的针头,医务工作者被污染艾滋病病毒的针头刺伤等都可传染艾滋病。 4.其他 目前尚不能证明空气、食品、饮水、食具、吸血节肢动物或日常生活接触能传染艾滋病。
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及母婴垂直传播。在正规的按摩场所,工作人员应该都经过体检,相关用品也应该都经过消毒,因而不会被感染。
但在那些不正规的按摩店,存在被感染的风险。极端情况下,如果工作人员未经体检而携带有艾滋病毒,同时在按摩过程中造成客人皮肤破损,这就有可能造成感染。
当然,如果按摩过程中客人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下发生了更“亲密”的不当行为,那么被感染的风险就会更大。
1998年,艾琳和她儿子的人生双双成为漫长的事故。在一场剖腹产手术后,通过医院安排的输血,她和新生的孩子一并感染了艾滋病。
此后多年,艾琳和儿子努力平整生活,一次次重建,却发现生活从未愈合。
2006年春节,8岁的李博腹泻不止。家里人找不到病因,奶奶坚持把李博往镇上的医院送,之后,医生认为他疑似肺炎,不断地给李博打吊瓶。然而治疗没有让李博的病情有太大起色,半个月后,年幼的李博瘦到了22公斤。一次,亲友来家探望,见孩子状态很差,又久病不好,提醒李博的父亲,孩子该不会生了大病,不能这么拖着。之后,李博被带到了深圳儿童医院看病。
他们挂到了一位权威专家的号。专家首先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接着,医生让护士给儿子抽了一管血,拿去检查HIV抗体。结果很快出来,医生问,孩子是不是动过手术?检查结果显示,孩子的HIV抗体呈阳性。
李博的父亲否认,医生觉得奇怪,又抽了一次血想再检查复核。那次抽血,父亲看见孩子因抽血喊疼,急得几乎和医院起了冲突。
再次检查的结果依然是阳性。医生断定,这么小的孩子,如果没有输过血、做过手术,更没有性生活,那绝对是母婴传染的。他建议李博的爸爸带着妻子,一起去查一次HIV抗体。
接到丈夫报信的电话时,艾琳刚刚从家乡辞职,在广东一所学校教书不久。电话里,丈夫告诉艾琳“出事了”,但坚持不肯告诉艾琳具体的诊断结果。直到听见艾琳声音颤抖,连连让他把话说清楚,丈夫才简短地告诉艾琳:是艾滋病。
等艾琳赶到深圳儿童医院的时候,医院已经给李博下了两个治疗指令。首先,不准许孩子走出病房,防止感染。其次,院方要求孩子转院到当时的东湖医院,深圳的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那里能为李博提供更好的治疗。
孩子是艾滋病,在这个小家庭投下了一枚炸弹。
艾琳和丈夫把手续办理妥当后,让婆婆照看好儿子,就立刻跑到网吧。他们开了机,立刻打开网页搜索那三个字。几页信息涌过来,一个词语特别醒目——世纪绝症。在艾琳印象中,当时她所看到的资料都支持同一说法:得了这个病,必死,且人人唾弃。他们快速结束了搜索,离开前,丈夫快速地删除了所有的浏览痕迹。
几天后,深圳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夫妻俩的HIV检测结果。艾琳是阳性,丈夫是健康者。
责任清晰地落到了艾琳头上。按照HIV病毒的三种传播方式“性、血液和母婴传播”推断,有可能是艾琳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给了儿子。而由于丈夫不携带HIV病毒,艾琳体内的病毒不可能来自丈夫。至于丈夫为什么没有染病,艾琳只能推测,跟传染的概率有关。
可是,自己又做了什么坏事呢?扪心自问了很久,艾琳想起了8年前的剖腹产手术。她在镇上生下白胖的儿子李博。从手术台上下来后,医院叫一个卖血的人进门,他和艾琳配型完成后,医院把他的400毫升血输入了她的体内。
艾琳跟李博的主治医生谈起这一经历,猜测是那个人把病传给了她。结果,医生用质疑的语气否定了这种猜测。1996年,国家已经命令禁止非法采集血浆,艾琳描述的输血方式按理说不可能被正规医院采用。他认为眼前的女人是在找借口。医生的不信任,让艾琳感受到强烈的病耻感。
把孩子送进东湖医院后,艾琳和丈夫抱头痛哭了一夜,以她当时的心境,更多是为儿子李博而哭。那是她和丈夫到广东发展的第三年,夫妻俩共有10万元存款。他们商量好,虽然孩子治不好了,但得把那10万元存款全部花完才作罢。
作为衡量艾滋病感染者能否生存的指标,李博的CD4(人体重要免疫细胞)值在入院之初只有每平方毫米17个,而一般来说,CD4低于每立方毫米200个意味着高危。经过诊断,医生确认造成李博每天腹泻甚至濒死的,实际上是艾滋病带来的两项并发症——卡氏肺囊虫肺炎和淋巴结核。
在东湖医院的艾滋病人专属病房,每天半夜都有送别死人的哀嚎。现在,年幼的儿子身患艾滋病,而且生命垂危,这一切都是作为母亲的自己带来的。这让她感到揪心。
在病房里,李博是最小的患者。一直折腾到那年六月初,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艾琳不敢放弃,她拉着丈夫决定继续和命运赌博,在找到一家公益组织资助后,他们将孩子送回老家,接受无国界医生的治疗。新的治疗确实改善了李博的症状。半个月后,他不再发烧和腹泻,胃口变得越来越好,要艾琳带他去上馆子。
孩子保住了。艾琳和丈夫的婚姻却在短暂的共舟共济后,彻底失去了纽带。孩子上小学期间,艾琳和丈夫分居两地将近3年。艾琳想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她说服丈夫回到老家,丈夫的态度表现出来了迟疑。他说想继续留在广东发展。
争执中,丈夫流露出了离婚的想法。他问艾琳:“你能不能主动提出离婚?”抛弃患病的妻子和孩子,这个道德负担对他来说太大了。遭到拒绝后,这个男人求艾琳放自己一条生路。
艾琳试图挽留,可最后还是作罢。作为条件,男人承诺离婚后每个月需要向孩子支付两千元抚养费,每年,要带孩子吃一次饭。
终于,这个家庭里就只剩母与子。还有潜伏着的HIV病毒 。
年幼的李博身体状态稳定下来后,艾琳开始为自己和儿子维权。这实际上也是生活所迫,治疗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钱。
在艾琳的老家,2000年前后爆发了艾滋病“血祸”。艾琳回乡时,几乎所有的马路和白墙上都贴满了“艾滋病”科普宣传海报。最早的艾滋病患维权官司,也出现在湖北。2001年,当感染者申某把给妻子输血的医院告上法庭时,他们一家三口都已是病毒携带者。最后,法院判处医院赔款。
2006年,艾琳在当地疾控中心候诊室里,和许多在同一家医院感染的感染者相认了,其中甚至有艾琳教过的学生,和九个在同一个县城分娩的妈妈。还活着的人们,商量着集体维权。
在当时,五万元赔款和每人数额不等的误工费是艾滋病家庭能够得到的全部补偿。对于艾琳来说,在得到补偿之前,她只能去政府机构蹲守,反映情况。
起先,这个陌生的地方让艾琳感到不安,她形容当时在县政府打探消息:“隔几步就感到害怕。”好在,她的蹲守在几日后有了收获。几天后,艾琳在厕所徘徊时,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照片上的县长,决定尾随他。等到秘书推开办公室的门,艾琳一只脚迈到屋内。
艾琳说:“我是艾滋病人。”
没有人说话。艾琳坐到县长面前,介绍完自己的身份,她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哭不是她出现在这间办公室的目的,她稳了稳神,从包里掏出“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县长按条例规定,帮助她和同伴恢复艾滋病人生产自救的能力。
在艾琳的讲述中,那次闯入的最后,县长当着她的面吩咐秘书,要恢复艾琳在当地的工作。不过,后来由于艾琳是艾滋病人的缘故,她最终也没有重新得到回校教书的资格,而是拿到了每月一千元左右的基本工资。
艾琳的维权持续了3年。随着一次次的反映情况,艾琳的感染者身份也在县城传开。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所有参与维权的感染者都在暴露与否之间做过挣扎。但最终他们达成一致——只有暴露自己,才能让诉求被看见。不过,把自己暴露出去的艾琳也领会到,李博患病的事情,她必须当成秘密守住,一旦暴露,很可能产生她预料不到的坏影响。
事后的经历证明,这是正确的判断。
在跟李博在同一县城出生且感染的孩子里,有9个在学校暴露了身份,随即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待。
在村里小学就读的孩子,被老师安排坐到了教室角落的座位。老师不给他批改作业,同学像看猴一样看着他。在镇上中学,有个孩子体育课上摔倒,流了血,体育老师顺手拉了孩子一把,触碰到伤口。体育老师打电话问疾控中心,惊恐地问自己是否感染。这些细节,不断加深着刻在这些孩子身上的烙印。
即使是确认健康的孩子,也无法如普通孩子一样自在生活。和艾琳一起维权的同伴中,有对夫妻都是HIV携带者,他们不认这个命,通过母婴阻断生了一个未感染的孩子。2010年左右,孩子在村里上幼儿园。风声走漏,其他孩子的家长得知消息后,集体反对孩子入学。双方闹到教育局,教育局让幼儿园必须允许孩子入学。结果,其他孩子都被家长转校。
看到这些孩子的经历,艾琳决意守住李博生病的秘密。奔走的生涯让艾琳变得强悍,她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给儿子构筑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
她着手让李博远离自己出现的场域,为此,在100公里以外的市里买了一套房子,想把李博送到完全陌生的环境读书。
开学之前,艾琳曾让李博去参与艾滋宣传活动。那是李博第一次认知自己身上的疾病。医生指着墙上的宣传海报对小朋友们说,我们的身体里面住着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会通过三种方式传染给别人。回来后,李博把这些句子说给了姥姥听。他说:“我妈妈输血感染了一种病毒,现在呢,我妈妈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我了。”姥姥从孩子奇怪的描述中,第一次猜到了真相,当着孩子的面绝望大哭。
见此情状,艾琳蹲下去盯住儿子,用严肃的语气告诉他,这种病毒叫艾滋病毒,但是你不能告诉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的所有人。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告诉其他小朋友,你就没有朋友了。别人就会对我们吐口水。
李博一下子愣住了,他顺从地点头,自那之后再也没跟别人说过这些话。艾琳希望李博尽量像个正常的男孩一样长大,可艾滋感染者要过上普通人生活并不容易。
做一名艾滋病妈妈,没有经验可供参考。离婚以后,艾琳曾让前夫给儿子买了一个篮球。可惜,李博对篮球并不感兴趣,那个篮球至今放在母子俩家中的阳台上,经过多年,晒蜕了皮。
后来,艾琳给儿子请过一位独臂乒乓球教练,想让儿子懂得精神的力量,儿子学了三星期,也失去了兴趣。唯一让艾琳满意的是儿子考上本地重点中学。
2010年夏天,李博放初一暑假,艾琳带上他,踏上了为期一个月的北京之旅。在艾琳的规划中,那是一次为教育李博而定制的旅程。头几天,艾琳带李博看完了所有听说过的展馆场所。从国家博物馆看到798艺术园区,从上午开馆看到下午闭馆,临近中午,艾琳怕沉浸感被打断,没有走出场馆,和儿子坐在休息区吃饼干解决了午饭。
旅程的重心是清华北大校园。艾琳雇了个司机带着他们逛清华校园,司机每到一处,都给儿子介绍杰出的清华校友,上了一堂四十分钟的思想课。出校门以后,司机还对儿子总结发言:好好学习,考到清华来!
尽管刚上初中的李博表现得似懂非懂,但母亲艾琳感到幸运——司机把最重要的话替她说出来了。
儿子李博一度是按照艾琳的设计成长的,这让她感到安心。艾琳不断对儿子强调学习的重要,但李博领会到的,更多是母亲严厉地要求自己“好好学”。她无法对年幼的孩子解释自己更长远的用意,她希望孩子足够努力,以便未来能够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
每当艾琳因维权或照顾孩子压力大时,会把自己关在卧室,打开电脑玩蜘蛛纸牌。这个习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李博理解为母亲忽视自己的标志。
一段时间,艾琳的保护给李博争取到普通孩童般成长、免遭歧视的成长空间。但这种严防死守的反面作用渐渐显现了出来。李博在学校没有朋友,他极度渴望友情。一次,他看见电视购物频道上的一个娃娃对着自己说:你好!他瞬间心动,央求母亲买给自己。艾琳看了眼标价:298元,心纠得紧,没有答应。他没有哭闹,坐到一边低头流泪。最后他还是得到了那个娃娃。母亲从网上买来了娃娃,实物很小,陪伴他度过了到新学校最初的三个月。
艾琳开始逐渐失去对儿子的控制。初二那年的某一天早晨,李博没有和以往一样吃艾琳准备好的牛奶和蛋糕,而是自己买了早餐。不久后的另一天,李博缺席了午餐。艾琳觉得奇怪,跑到儿子班门口去找人,迎面撞上李博正拿着面包走回来。艾琳脸一沉,问:“你是不是去网吧了?”李博不敢做声,艾琳从孩子的沉默中猜到了答案。
晚上,李博放学到家,艾琳一个耳光把他打得跪到地上。近乎疯狂地,艾琳连扇了李博几个耳光,吼道:“你不好好读书,要怎么生存?以后上街拉车都没你的份!”
李博没有争辩,他不说话,用膝盖撑着地面,跪得很直。
艾琳觉得,李博的路走偏了。此后,她不再给儿子早餐钱,要求儿子必须在家里吃自己买的牛奶和蛋糕。这才能让她放心。
直接的对峙发生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李博打开艾琳卧室的房门,直接掀开艾琳的被子,把棉被抱在怀里。
腊月的夜晚,这个初中生直视母亲,要求母亲把父亲每个月给的两千抚养费给自己:“这样你就不用每天给我买牛奶和蛋糕了。”艾琳立刻拒绝:不可能,我是你的监护人。
李博没有再坚持,他把被子还给艾琳,和母亲对看了一会,作罢了。
后来看,那并不意味着李博甘心地回到了母亲的庇护之下,而是更为沉默地坚持己见。他开始自由决定自己翘课还是读书,在家还是在网吧。但无论是逃课还是呆在教室里上课,他都没有同伴。他的青春期里只有自己,在学校里交白卷,在家里被母亲骂,都没有人分担、倾听。即使坐进了网吧的卡座里,虚拟世界里也没有人与他同行,他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李博梦想着逃离母亲的掌控,并付诸了行动。他曾揣着400块钱离家出走七天七夜。一开始,他到网吧扎根,每到吃饭时间,只买便宜的小零食充饥,以便多一些钱打英雄联盟。后来附近网吧夜晚失火,烧死近三十人,公安部门禁止网吧晚上营业,李博不得不找其它的地方过夜,或者回家。如果选择后者,他很可能需要面对母亲严厉的责备。
没有多余的钱住宾馆,李博宁愿在南方冬天的街头晃荡。他先转移到麦当劳,麦当劳在凌晨关门后,就去街头游荡。时隔多年,他依旧记得自己在室外坐下一会就冻得受不了,很难相信自己当时在马路和巷子里连走了八小时。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李博也没有忘记按时吃药。他算着艾琳每天出门的时间,偷偷跑回家取药。早晚各吃下两枚药片,间隔十二小时,这是保证病情不再复发的底线。他从来都明白自己身体里的病毒。
14岁的李博在第八天花光了400块钱。别无选择,他回家等着艾琳一顿大骂。好在艾琳看见儿子瘦得脸塌了,一句没骂出来。在寻找李博的8天里,艾琳只是想不通,自己如此地爱儿子,为什么儿子就是不愿意回家。
艾琳自那之后尝试了很多方法,想把李博“拉回正轨”。她把李博从重点中学转学到家乡县城,让他降级到初二重新学习,希望回到熟悉的环境、降低他的学习压力。但这无济于事。
最后,一次艾琳在各家网吧找不到儿子身影时,拨下了110。她措辞激烈地对县里的警察说:“我儿子是艾滋病,我现在要找到这个孩子,让他喝药。”
在警察的帮助下,艾琳在一处网吧找到了李博。她把李博从网吧的座位里拽到了大街上。警察走后,李博转身就跑。艾琳在后面跑跑走走,10分钟后,她跟丢了李博。
站在街头,强硬的母亲第一次冒出了放弃的念头。那之后,她不再约束李博,李博回了家,在本地一所被认为是“末流”的学校读完了高中,每周,大概有4天会光顾网吧。
读初中时,李博听说,高一读完以后就可以去当兵。这成了他的人生目标。他想让自己意志坚定些,觉得一旦获得了毅力,退伍归来以后,生活就是崭新的了。
李博的新目标,让母亲陷入新的为难。艾琳知道军队不接收感染者,又不敢扑灭儿子的希望,最后,她只能拖着儿子,答应他:“等你满18岁,咱们再考虑这个问题。”
当兵的愿望让李博的生活似乎有了动力。他决定报名校体育队,每天早上跑步、举重、练习力量,很少去网吧。不到一年,他发现自己的腹肌有了阴影,摸上去是硬的,隐隐有八块。他身高一米七以上,体脂率10以下,一旦练出了肌肉便显得十分强壮。
高二下学期,李博班上开始有同学报名参军。那时候,他才被母亲告知,自己的状况不会被招收。艾琳告诉他,可以每个月给艾滋病公益大使写信,呼吁重新考量这项规定,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写,一直写到高考前。母亲安慰他说,相信这可以推动HIV感染者当兵的进程。
李博听不懂这些,也没有反应,这让艾琳不再为难。
李博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形容自己像一个“死刑犯”。在体育队里,没有其他孩子被照顾得跟他一样细致。母亲时常当着所有队员的面给他送饭。在一群队友的注视下接过饭盒、打开盖子的那一刻,李博说,像是在接受某种给“犯人”的恩典。
艾琳对此毫无察觉。她有属于自己的焦虑——随着李博日渐成长,艾琳察觉到让儿子完美融入人群的愿望在逐步收缩。由于艾滋病李博无法参军、报考事业单位;由于成绩不好,他无法读好大学。这个孩子十八岁后的人生走向依然模糊。
她最后意识到,仅仅在当下,母爱也无法温暖儿子。在艾琳身上,一种罕见病已经发作。不到三年眼睛发病数次,最后,一只眼睛失明。医院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
艾琳决定调整自己的状态,放开对儿子的控制。她鼓励李博去谈恋爱,用自己的社保卡专门去给儿子去买了一盒避孕套,放在儿子床头。后来,李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对方也是艾滋病友。
2020年春天开始时,艾琳、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一起在湖北省某市的房子里隔离。三月某个晚上,李博准备在客厅餐桌上摆火锅。他把切好的菜端过来,艾琳还在桌上写毛笔字,说,再等我三分钟。他回了两个字:恶心。
这是艾琳第二次听到儿子骂自己。第一次是一月份,艾琳收到儿子发来的微信,询问能否支援他一笔练车费用,艾琳第一次拒绝了儿子的请求。随后,他发来两个字——“恶心”。
艾琳毫无防备。这个身上流淌着自己的血,辛苦抚养22年的儿子,会用这样的字眼咒骂自己。没过多久,她又听到儿子说“恶心”。
作为母亲和孩子,是被什么弄脏了呢?
艾琳觉得刺痛,她哭着问儿子:“为什么要对最亲的人说这样的话?”几天后,李博在微信里向母亲道歉。
艾琳始终无法释怀,她说不出来,显然道歉是不够的。这逼急了李博。他从门厅快步走到阳台上,拉开窗户,猛地把半个身子从窗户探了出去。艾琳吓坏了。
这次冲突之后,艾琳决定对儿子彻底放手。李博已经22岁了,除了无忧无虑那8年,剩下的时间,自己带着他走过的都是淤泥。她与儿子的人生,其实早已踏空。
在淤泥中挣扎的日子,确实挺恶心的。作为母亲,艾琳累了。
家里依旧是往日的模样。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是几年前,艾琳让儿子挂上去的,地图旁写了一行字:艾琳和儿子的世界足迹。初一暑假的北京之旅后,母子俩再也没一起出过远门。
想通之后,艾琳把存折给了儿子,她嘱咐李博驾照已经考了三年,再不拿,就要再来一遍。
2020年10月2日凌晨四点,去北京看病的艾琳从火车站里走出来。儿子和他女朋友站在门口,接过艾琳的箱子,指着一辆蓝色小汽车说,妈,我来接您。
这是儿子拿到驾照后行驶的第八天。为了表达道歉的诚意,他在前七天练车,走完了整个市区。看见有司机加塞,他像个驾驶多年的司机,把握十足地告诉艾琳,这时候我就算撞他,也是他负全责。没开过一天车的艾琳赶紧劝阻李博:“儿子,车不是这么开的。”
出城以后,乡里的路全黑。这辆租来的车小心翼翼地上路,从市里驶向在农村的姥姥家。李博打开车灯,从黑暗里开到天亮。
*为保护当事人,艾琳、李博为化名。
- END -
撰文 | 石润乔
编辑 | 温丽虹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