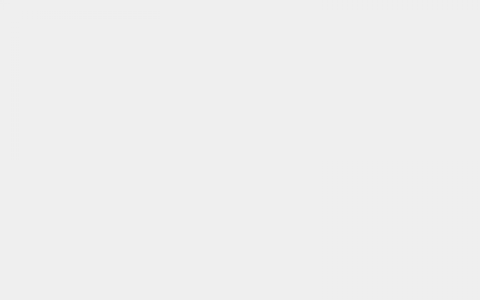连续一周赶早,上午,下午,晚上,连续的早读,上课,改作,开会,夜自修,彻底摧毁了八月份辛苦锻炼的结果。牙酸,头痛,脑涨,失眠,肚胀,焦躁,忧虑,悲观,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症状和情绪不断地出现在脑海中。老王说,我应该去精神科看看医生了。有可能得了抑郁症。我也这么觉得。再这么下去,我会愤世嫉俗,会排斥各种工作,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像自己了:开个会,我抗拒;加个检查,我反感;每天的早读,我厌恶;一周两晚夜自修,我疲累不堪,深恶痛绝。再想起接下来要上的提高班,整个情绪恹恹的,仿佛是在炎热的夏天,掉进一条臭水沟里,又闷又热又湿又臭,怎么也爬不上来。我下定决心,下周一,下周一,一定要抽出时间,去看看,必要时,也许会选择吃药。我讨厌这样的状态!而在周一到来之前,我得尝试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于是,我选择了运动。
所以,那天,我是来锻炼的。
我不是心血来潮。八月份,一天不落,雷打不动,从最初的半个小时,到后来的两个小时,从气喘如牛,胸闷不能自抑,到挥汗如雨,气喘吁吁,再到舒坦通透,每个毛孔的呼吸中都带着欢愉,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任何工作。而这份自信,历经一周,每天十来个小时的打磨,一朝回到解放前。想想还是挺郁闷的。于是周五,我又开始折腾了。这一折腾,把一周的郁闷都通过汗水蒸发出来了。于是周六,再接再厉。于是周日,巩固成果,为未来的一周打好坚实的基础。
其实那晚本不是悲催的一晚。那晚,约了多次,又因工作的问题爽约了多次的小严,终于姗姗来迟。我终于有熟悉的小伙伴儿一起流汗了!跨进麦迪逊健身会所的脚步,都觉得轻快了不少。
那晚的课,说是网红运动和尊巴。这个我知道,动作不难,运动量也够,不会太剧烈,又有一些味道。可惜的是,教练换了,不是慧珠,而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年轻姑娘。
我喜欢站在最前排,这样可以清楚地看见教练的示范动作,不像后面,隔着学员的身躯看教练,总有一种被化灰的烟火气呛着的感觉,不清不爽。
节奏欢快的音乐响起,踏步,前进,并步,后退;踏步,前进,并步,后退……动作简单而欢快。“来来来,跳起来,跳起来……”充满魅惑的声音有力地在耳边响起。我确实感觉到了无法言说的喜悦,这种久违的感觉,让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在简陋的体操房,和沈老师以及队友在寒冷的雪天,穿着一件运动卫衣,挥汗如雨的日子。多好的律动啊……
正当我开始跳踏步的时候,猛然间,左脚脚踝处好像被一刀片突然扎断,好像肉里突然少了一点助力,脚一下子失去了支撑。我不得不蹲下来。疼痛,在蹲下来的一刹那,猛然间席卷过来。到底是谁踩了我?为什么不跟我道歉?我愤愤地,却又努力平静心情,朝后看去。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离我最近的那位,是在一米开外的后方,她正专心地跟着教练跳着,然后一脸愕然地看了看我,随后又继续甩臂,踏步,跳跃……
我以为我只是崴了脚,却不料怎么也站不起来,一阵又一阵的剧痛,我只能蹲坐在地上。小严过来了,教练也停下来了,后面的学员也凑上来看情况,不久,经理来了,慧珠也来了。那个小身板的慧珠,背着我走到隔壁私教教室,有人拿来一袋冰块,敷在脚踝处。可怜的脚只能往前垂着,看着迅速发酵的脚背脚踝,以及时不时奔袭而来的剧痛,我终于忍不住哼哼唧唧出来了。
所有人都安慰我,这个没啥问题的,冷敷一下,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经验。我相信这个经验的价值。我也愿意相信,我只是崴了脚,仅此而已。可我无法说服自己,那一刀下来的感觉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忐忑不安,我得去医院。
受伤的左脚就好像枝头黄透的银杏叶子,轻轻一晃荡,就会飘飘扬扬地坠落到地。我不敢晃。脚踝处胀得失去了知觉,偶尔晃到了,时不时袭来的刺痛又告诉我,我还有左脚。唉,罪孽啊!
且不说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但就轮椅的感觉,就已经糟糕透了。对于轮椅,我没有好印象。
第一次坐的时候,是17年8月,那是一个灰暗的日子。吴推着轮椅,从三楼病房到 B超室,静静地等待结果。三天后,六个月大的胎儿因破水,没了。好不容易走出阴影,却不料这次又来了。丽推着轮椅从急诊大门走进诊室的时候,一分钟的路程分外漫长。那种不能左右自己的感觉,真真糟糕透顶。但愿这辈子再也不用轮椅。
严夫,乃小严老公。小严陪我来到医院,她喝得微醺的老公说什么也要到医院看我这个大姐,顺便指责一下小严。
我其实感觉挺尴尬的:你看吧,好好的锻炼,又没有打篮球那么剧烈,也不曾跳高跳皮筋,只不过在踏步变小跳步的时候,在想不到会出问题的时候出问题了。一想起这个,我就特别尴尬。要知道,我曾经是健美操队的,健美操队的啊!我无脸见沈老师了!
严夫一来,就急着帮我张罗:排队牌已经显示名字了,为什么看不到,那么多人呆里面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而要在外面等,为什么轮到了,还要等那么久……我记得,严夫同志有很多很多的小不满和为什么,当然,还有出现频率超级高的“我老婆”:我老婆就是好,老婆你说对吧,我老婆……一直到现在,想起严夫,“我老婆”三字,便如唐僧的经,一遍又一遍在耳边回响。
面对严夫的话痨,小严一脸无奈。每当严夫飙高音量,小严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这是医院,要轻点,轻点。严夫好像总听不见似的,要么说没关系,要么眼一翻,牵着小严的手,或轻抚或轻按,然后再继续,一边说,一边看着小严笑。话里话外,除了医院办事不力,就是小严陪着我,才害的我受伤。我不断解释不是小严的问题,严夫一定要说是小严的问题。我看着严夫看着小严的专注眼神,和小严无奈的宠溺般的笑,嗯,这么说吧,就好像吉林的雾凇,白净而美好。
小严和严夫,是一对幸福的小夫妻。他们,是来给我力量的。
带着眼镜的医生拿着CT,对着日光灯,斜着头看了一下,嗯,骨头没事。你那块地方是跟腱。冰敷24小时就好了。
可是我感觉有刀片切了脚后跟。会不会跟腱断了?
眼镜医生哑然一笑,不可能,跟腱断了,你还会那么舒服?
呃……我正想继续问,又找不到合适的问题,想想算了,还是先冰敷吧。见眼镜医生打开了电脑,他是要开药方了。这个时候,门外来了一护士,附在他耳边讲了一句话,他立马神色匆匆,起身走人,没有任何交代。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他都没回来。我好像被凉在那里了。我很着急。那会儿已经是快十点了,女儿夜自修,早已放学,老吴出差,她钥匙没带,我托小严把身上唯一一把家里的钥匙送给她。她打了两通电话,一通是告知我,她已到家,另一通,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一个小姑娘,深夜,独自一人在家,第二天一大早,她还得早起上学。想起这些,再看看陪着我的丽和小严,一时间难以平静。眼看着诊室里病人越来越少,眼镜医生还是没来。好在丽机灵,把病例给了对面的花白头发的医生。
老医生又瞅了瞅片子,再看了看脚踝,再一次确定,我只是扭伤而已,冰敷24小时后再喷点诸如云南白药之类的药物即可。我再一次重申,我有刀切的感觉。同样,老医生再一次告诉我,跟腱应该没断,不然,你没那么舒服。
舒服?我不禁哑然。都肿的像发酵的馒头,冰敷那么久,才退了些。脚踝无法自由转动,想动一下,就好像被折掉的枝桠,就那么悬挂在枝头上。再加上时不时席卷过来的揪心的疼痛,何来舒服啊?也许这种疼痛,在不断流血昏迷的急诊科,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想起这些,终于有点能接受,我那么舒服的诊断了。
白发医生终于娴熟地把就诊卡放在感应器上,一闪一闪亮着的指示灯给了我无限的希望,我终于可以拿到药物,可以回家,可以让辛苦陪了我一晚的朋友休息了,也可以让一直在家等着我回来的女儿休息了。“呃……”白发医生这一声,瞬间打碎了我所有的希望:他的电脑,没法给我开药。原来是一病看两医的问题。他起身的时候,眼镜医生终于回来了。
我拿到了两种药,一种外敷,一种内服,都是活血的。
十点半,到家,辛苦了一晚的朋友也回家了。而我,一跳一跳地从门口跳向房间,一不小心,趔趄了一下,左脚着地,撕拉的疼痛,如月牙泉边的沙子,吹的我耳窝眼角鼻孔发际,无一处不是沙子,无一处不疼。这份疼痛,又让我想起刀切的感觉。
可是医生说过,我如果跟腱断裂,还有那么舒服吗?我等着24小时后的舒服。
伤后24小时之内要冰敷,这是常识,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慌张中忘记。正如我。
在医生的提点之下,总算不折不扣地执行起受伤24小时内,必须冰敷的医嘱了。
冰敷最难的是睡觉。我没有买专门用于冰敷的袋子,现在想来,有点后悔,家里一定要准备一个冰敷袋,以备不时之需。我用的是食品保鲜的冰袋。它在冰箱里冻成了块。就是这一块一块的冰袋,折磨死我了,棱角分明,膈得生疼。好不容易等它柔软了一些,没过多久,又不冷了。那晚在醒醒睡睡中,那天在换来换去里,熬过去了。只是,等肿块消失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悲哀地发现,脚跟上方后面,有一块地方凹陷进去,没有牵扯力量了。不详的预感再一次占据了我整个大脑。我总有被漫天黄沙淹没口鼻的惶恐。第二天,必须找专业的骨科医生看看。
受伤后第三天,去了市一医院,应医生听完我的话后,直接带我去了B超室。B超下,他指着中间黑色的部分告诉我,你的跟腱,断了。
预感成真。我没有半丝喜悦。那怎么办?
应医生帮我联系上海的专家师傅,咨询能否做微创。七点左右告诉我,微创效果不佳,建议做传统的开放性手术。
八点,去了台州医院,班长帮忙联系了吴医生。他让我趴在病床上,两手捏住左右小腿,跟老吴说,你看,左边连反应都没有了,肯定断了。去办手续吧。
就这样,我又住院了。
9月12日
要做手术了。我其实想告诉边上的人,我一点儿也不紧张,我有经验。可当我面对父母的时候,我说不出一句话,只对着他们笑了笑。
手术室的大门打开了。一位女医生接我进去。躺在移动病床上,看着她拿起注射器,配置药水,挂在床头架子上,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掉,女医生拿起针头,微笑着跟我说,忍一下,这个针头比一般针头要粗一点,打的时候会有点疼。
我知道。我懂。年内做宫腹腔镜手术的时候就已经领略过了。可我仍然忍不住打颤。针头扎进手背表皮,不断搜索着静脉,在两三次探索之后,可爱的血终于在针尾溢出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很开心地跟女医生闲聊着,她不断地问我各种问题,姓名啦,单位啦,工作啦,生活啦。术前这样的聊天确实可以让人放松不少。
不一会儿,一位男医生过来了,拿着一个长约20厘米针头的针管,叫我右侧位卧着。深呼吸了好几次,充分做足了思想准备,终于,针扎进去了。继续深呼吸,嘶嘶啦啦深呼吸,嘶-呼-嘶-呼深呼吸,针头很不老实,由浅而深。那一针应该不长,但却感觉过了半个世纪之久。完了后,男医生嘻嘻笑着对女医生说,她很不会熬痛。
呃,我有给他打这个针的冲动了!无奈身入手术室,只能把自己当作一只纯粹的人形动物。
进入麻醉室,消毒,聊天,深呼吸,好像前一秒钟还在聊天,后一秒钟,便毫无印象了。
对于疼痛的记忆一直不那么美好,所以我一直很抗拒疼痛,术后选择了止痛棒。
恢复意识,回到病房,护士告诉我,如果有疼痛感,可以摁一下开关。我问她可以摁几次,她说,至少二十来次。我再问她,什么时候摁。她说,你感觉有点疼痛的时候就可以摁了。我很听话,略有疼痛的时候就摁。第一天,摁了三次,第二天早上,摁了三四次,中午,摁了十几次,一到两分钟就摁,不幸,麻醉失效了!!!我坠入了地狱。
疼痛像丛生的荆棘,更像倒钩的芒刺,不断拉扯着神经和肌肉,一颤一颤。早上查房的时候,我还特地问了护士,止痛棒里还有没有药水。护士说,满的。我以为我痛感神经对麻醉免疫,以往确实如此。不过这次没用了。无论我如何摁着止痛棒的开关,止痛功能好像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停留在一呼一吸之间,却始终无法达到疼痛点。脚踝处的疼痛不断扩大,我和妈妈已连续呼叫护士站三四次之多,表达了同样焦灼的渴望。而护士,忙的身影不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缓缓地在疼痛中,一点一点,从地球北端,慢慢踱到赤道,再踱到地球的南端。妈妈再一次跑到护士站,在焦急的申诉后,终于拿到一粒止痛药。我把它当成了救命的稻草。可惜,这根稻草一点也不体谅我的难处。它还是断着,丝毫拉不出疼痛这个魔鬼。我依旧疼着,冷汗直冒,哼哼唧唧,小声啜泣,眼泪直流。妈妈再一次跑到护士站,略带着哽咽的声音,告诉护士我的痛苦。然后,我看见一位美丽的护士,举着一大针可爱的药水,给我肌肉注射。止痛药水啊,终于在注射后的半个小时,起了大作用。这是我第一次喜欢上痛苦的肌肉注射。
后来,护士终于忙完手头工作,叫上终于忙完手头工作的麻醉医生,然后告诉我,止痛棒里早已没了药水。我实在搞不清楚,查房的时候还告诉我止痛棒里的药水还瞒着,为什么会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内消失不见。麻醉医生一脸无奈,像看着一只小白鼠,然后说:药水一直在流,你摁下开关的时候,它的流速会迅速增大。摁的次数越多,药水流失越快,其流速是平时的十倍。你摁了那么多次,它老早就没了。
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当初那个护士会那样肯定地回答我呢?
第二天晚上,我挂了一瓶止痛药水。
第三天早上,一瓶止痛药水。
第三天晚上,一瓶止痛药水。
第四天,我说我能忍住疼痛了。早上又挂了一瓶。说是晚上还有。在我强烈要求之下,晚上的止痛药水取消了。疼痛,已渐渐向我挥手告别。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除了偶尔有的酸痛,我已经不再被疼痛折磨了。
但愿此生不再有疼痛!
不想说,又不得不说。这种感觉,实在糟糕。最初的半个月,不方便,太不方便。
跟腱靴实在是一个好东西。
三周过后,我开始穿跟腱靴,从此结束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日子,也告别倚仗凳子当作左脚一拐一拐行走的日子。去刷牙,上厕所,逛阳台,终于结束终日躺在床上的日子,每天,我可以有短暂的时间,一瘸一拐,慢慢挪出这个两平方米左右的天地,去看看窗外的太阳,吹吹门外的暖风。
四周后,我开始户外行走。第一次走在大街上,摇摇晃晃,高高低低地慢步移动,那天的风不大,但足以吹动发尾,扰乱新生的杂发。妈妈搀着我,俩人一起摇摇晃晃,走在小巷里。还没等我享受完行走的自由,便有令人不快的目光追索而来。这种目光,每天跟着我,令我难堪,也令我恼火。
我不记得这是哪个人的目光,也许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油腻男人,也许是一个染着黄发顶着黑眼圈的妇人,或者骑着车,或者逛着街,或者牵着孩子,或者拎着菜蔬,他们或迎面而来,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盯着我的左脚,再皱着眉头看我的脸,或由后赶上,转头盯着,一眼不眨,从下打量到上,又从上打量到下,然后盯着我,一脸鄙夷,偶尔遇上几个好心的男女,不断询问,你脚怎么了?哦,受伤了。怎么受伤的?锻炼啊。锻炼怎么受伤的?……连续追问,全然不顾我已酸累。问清楚后,转身离开。每每遇到这样的目光,我总感觉如芒在背。晚上回家,翻来覆去地想,想再次遇到这类问题该怎么办。后来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哼哼哈哈,一笑走之。遇到不善的目光,直接瞪回去。
走了三四天后,可以连续走几百米了。从那时起,开始不间断练习,只要脚还能坚持,就努力复健。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上街,还是不习惯那样的目光。
那天中午,女儿班有同学看见了我。有个小男孩兴奋地高声喊起来:“看,吴的妈妈,钢铁侠。”紧接着,一群孩子隔着窗户看向我的左脚,“钢铁侠”此起彼伏地响着。那种不加掩饰的惊呼,没有上下打量,也没有故作关心,我努力加快脚步,尽管力不从心,却不觉得煎熬。
此后,跟腱靴依旧跟着我上街,街上依旧有各种目光,我依旧不太喜欢长久的打量的目光,但不管怎样,跟腱靴给了我行走的自由。
每每脱下它,我都要尝试两脚站立。走着走着,左脚慢慢有了一些力量,不再左右大幅度摇晃。孱弱的左脚渐渐有了一些力量,甚至我可以尝试用半个身子的重量,偶尔压一下它。
不知道我还要穿着跟腱靴走多久,也许一个月,也许一个多月。光明已在眼前,多走几步,就离正常行走近了一步。
跟腱靴,钢铁侠,继续赐予我力量吧!
第一周,脚尖动动,脚踝石膏固定。做抬腿曲腿等运动。
第二周,与第一周差不多。十天后,可以卸下石膏,做做脚踝运动,脚尖往上,努力使脚背和小腿成90度角。这一步我不知道要做,结果复查时,调整石膏角度,疼得我全身冒汗。
第三周,继续脚部运动,努力使脚背和小腿成90度角。周尾,拆线。
第四周,第三周买的跟腱靴,复查的时候跟医生提起。吴医生当晚就教我怎么使用。手术后第21天,开始两脚下地。房间里行走。
第五周,复查后,恢复不错。开始户外康复训练。第一天时走800米左右,回家累趴,一下午不能动弹。第二天继续,结果大腿使不上劲。第三天能走到附近菜场,约六七百米,然后坐在那里休息了十来分钟,再走回家。10.20,邻居看到我走路,表扬我终于走稳了很多。已能连续走1000米左右。速度不能作要求,摇摇摆摆像鸭子。
第七周复查。
备注:
我的朋友们,如果你想问我怎么弄去的?为什么不小心?看你还敢不敢锻炼?现在如何?恢复得怎么样?要不要帮忙?……那就请看前面的文字吧。我不想再反复回忆当初的经过,那样会让我手足无措深感懊恼,说多了,总觉得自己会成为另一个祥林嫂,絮絮叨叨,命运悲惨。也不要说我是否适合运动。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正如跟我同时受伤的一百里外的姑婆家的女儿,开车回家,从车上下来,一不小心,也是跟腱断裂。
如果你要抽时间来看我,也请停下你匆忙的脚步。你有自己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不愿意因我的问题,而扰乱你我各自的节奏。我接收你们的祝福,但也想保持自己的空间。就目前这样的日子,挺好。再过一个多月,我又可以重回工作岗位。
我记下这段经历的目的,是想告诉朋友们,请珍惜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幸福。而我现在,正在往这条路上行走。
跟腱断裂这种严重的伤病在国外治疗更好一些,而医药费则会由广东队全程负责。
马尚可以说是广东队的重要外援,而马尚的跟腱断裂也让广东队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马尚就算是恢复了健康跟腱断裂所带来的影响也会伴随终身,因为跟腱断裂这种严重的伤病毁掉的是运动员的运动爆发力,所以我觉得就算是马尚恢复了健康,也并不一定能够继续留在广东队效力。当然广东队也会全程支付清马尚的医疗费用,因为马尚是为广东队效力时受的伤,所以广东队也并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抛弃他。
一、国外在治疗跟腱断裂伤势方面会比较专业一些。国外有很多知名的运动员都出现过跟腱断裂的伤病问题,不过在通过专业的治疗以后,有些运动员依然能够在赛场上打出优异的表现。因此我觉得为了马尚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让马尚去国外治疗才是最合适的,因为运动员的伤病问题如果处理存在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运动员一辈子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二、国外的恢复治疗方面会比国内更专业。国外的运动员之所以能够很快的回到赛场,就是因为在恢复治疗方面做的非常的详细和周密。因为只有经过系统性的康复训练,才能够让运动员的运动机能得以很快的恢复。而国内在康复训练等领域还处在空白阶段,因此选择去国外接受康复治疗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三、跟腱伤势要经过漫长修养。跟腱伤势不等同于其他的伤病,因为其他的伤病只要经过康复训练就能够重新站在赛场之上,而跟腱伤势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运动员就会很难再重新站在赛场上。因此我觉得广东队这一次对待马尚的跟腱伤势一定会非常的谨慎,如果马尚以后再出现此类伤病的话,马尚的职业生涯也将会提前宣告结束。
祝愿马尚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因为马尚在赛场之上是一位非常用心比赛的球员,但是现实给了马尚致命一击。不过我认为这样努力认真的球员并不会因为一次伤病被彻底击垮。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