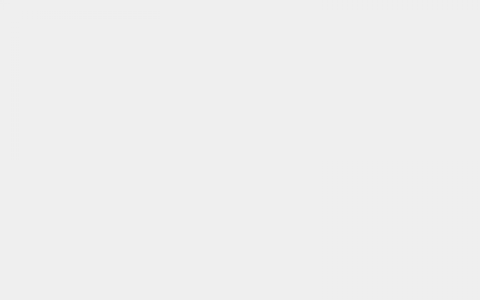第一次解剖尸体是在《局部解剖学》课上。
解剖学在实验楼1楼上课,教室暖气不好。当我趴在不锈钢的大柜子上上课,上到第三节课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不锈钢的长方体大柜子是可以打开的,而里面,就是尸体。
记得,我前一节课瞌睡,直接趴在上面睡着过一小会儿...
第一次解剖时,有点不适应。一是,福尔马林气味太大,很难忍受;二是,一想到我们的课本下面就是尸体,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谢谢那些对我的医学生涯做出重要牺牲的人们!默哀...
解剖尸体的时候,8个学生一具尸体,每次2把手术刀。我们组是一具中年男尸,体型偏胖,很完整。真的很完整,以至于,到学期末,我们把他解剖完毕,竟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死去的...
全身皮肤完整,各脏器完整。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莫非是急性心梗,或者脑出血?
真正解剖尸体的时候,其实大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能是之前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已经有太多的小动物做完铺垫了。有时候,有的小组解剖的比较慢,以至于傍晚的时候,偌大的实验室就剩下没有几个人了,尸体数目比学生都多,但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有时候静下心,你会觉得他留给你的,你下辈子也报答不完。当心里坦然的时候,你会觉得即便遇到鬼,也会是好鬼....当找不到某根神经的时候,好几次,我祈盼那个尸体能自己动一动,告诉我那个神经在哪里...
学期中的时候,有一次路过学校法医鉴定中心,看到做尸检,就凑过去看。竟然是我们的老师在做,顿时震惊了!尸检,真的和解剖尸体完全不一样(不想描述了...)。家属在门外等候着,一脸严肃又害怕又复杂的表情,至今仍能清晰浮现。
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后来上伦理课或者讲述医疗纠纷的时候,每当说到尸检,我就会想起那个情景:那天,天真的很冷,尸体,就在台上那么躺着...
我挺庆幸我后来在医院里面定在了儿科。
在医院第一次抱着死亡的新生儿宝宝给家属看的时候,我努力的想让孩子展示出一副笑脸。最后,勉强成功了。爸爸妈妈哭成了泪人。我站在旁边,不知所措,最后,也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一个护士把我拉到一边了。再后来,上级医生批评了我;后来的后来,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我觉得我对尸体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了。
如果你是问尸体!那么他不会疼!如果你问他的亲人!那会疼!~
假如是问解剖他的人!那他不疼!只会着急!半天切不完!~
谢谢!~
分类讨论到此结束
男人突然醒了,最先印入眼帘的是五个穿白衣大褂,拿手术刀具的医生。
第一反应是疑惑,怎么了,自己生什么病需要动手术吗?
又听着一个医生说,正面的皮已整个切除,现在需要解析肌肉。
对这句话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的男人,突然瞥见自己的脖子以下的皮已不见,露出分不出哪是哪的一片血肉模糊。
顿时一阵惊慌。想说话,想挣扎。却发现一句话也说不出,也移动不了丝毫。只剩下清醒的神智与圆睁的双眼。
又见有四个医生开始拿起手术切刀,一点一点地切割着解剖着自己身上的肌肉。有的拿着刀,顺着肌肉的纹理在他的肚子上一层一层地切片着。有的在他的手臂上,小心地钻过骨头和血管,把他的肌肉剔除出来。 有的则大胆些,在大腿上刮削着。貌似还有一个拿着把很小的刀,在他的脚上雕刻着。另外还有个医生则举着摄像机在拍摄着这骇人的整个过程。
此时的男人情绪已超越了害怕,惊恐,绝望。反倒是这太过震撼的情绪,产生了另外一种自我保护情绪—恶心。对恶心。此时的他只想象着这个肉体与自己无关,只是一摊猪肉,被人切割的猪肉。嗯,这个切割方式确实很恶心,很恶心!
因为反正虽然被切割,貌似也感觉不到疼,只觉得像是补牙时机器钻牙齿的麻麻的感觉。反倒是肌肉被刀具翻动与切割下来的感觉却很灵敏。以至于虽然肚子以下他并不能看见,却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些医生的每个动作。
把男人身上的每片肌肉与脂肪切除完之后。又听着一个医生说:“好现在一起帮忙打开胸腔!”
于是两个医生一左一右地站在病床两边,大力却平稳地一起朝相反方向用力。伴随着韧带撕裂的声音,胸膛中各个内脏器官呈现在大家眼前。
事实上男人有些害怕又有些好奇于自己的内脏呈现。于是他也使劲地眼珠子朝下,瞟着自己胸口的这一堆东西。
虽已血肉模糊,但最明显的是那颗噗通噗通跳的心形肉团,一定就是心脏了。既然能睁着眼睛看自己的心脏,真是不可思议呀。那样子就跟平时吃的鸡心差不多,不过大了很多倍。
那在心的两边的跟猪肺大小和样式差不多的东西应该就是自己的肺了。
眼神使劲地往下瞟,因为血液翻涌的缘故,肝脏与胃的等其他器官,并不完全分的清。
男人正沉浸于自己的器官探索时,那个拿摄像头的医生说,可以开始实操了。
于是四个医生的四双戴着手套的手都在男人的胸腔内掏弄着。
他们轮流着对着男人的器官,或摸,或捏,或翻看。时不时也用棉布擦拭涌出来的鲜血,以防止影响到他们的观察。后来甚至还拿来放大镜,在每个器官的经于络、纹和理之间细细地观赏着。
男人照样还是感觉不到疼痛,只是那每个动作每个掏弄他都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因为有些麻,有些痒。甚至医生用双手撸他的大肠时,他都有些痒得忍不住想笑。如果当时他能笑的话,一定会笑的。
所谓的实操好一会后。那个拿摄像机的医生又说:“好了,现在可以,翻一面,解剖后背了。”
于是四个医生一块动手将男人翻了一个面。
事实上男人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他就面朝着床,什么也看不见了。或许他是不喜欢因看不见而导致的更深的恐惧,也或许只是因为黑暗阻挡了他的好奇心吧。
现在男人只能竖起耳朵听了。因为现在只剩下耳朵能知乎自己的命运了。
“试着解剖脊椎!”
“对,先在脖颈处切一刀,将脑袋与身体分离!”
这是男人的脑袋与身体在一起的最后一秒。
随着刀起刀落的一瞬间,手术房内传来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拿刀医生瞬间吓得手上一抖,刀子飞落在地。
其他几个医生也面色僵硬,面面相觑。
这笑的声音有些沉闷。像是包在棉絮里一样。医生们立马反应过来了。是——那个首体分离的男人发出来的。
医生们顿时个个都竖起了鸡皮疙瘩。
但是心中又很是疑惑,怎么已割断脊柱与神经,还能笑得出来。
其中一个医生壮起胆子,拿个手术刀,用力地将埋在被单里的脑袋一扒。
脑袋在床上翻了两下,滚落在地,滚到了医生们的脚边。
伴随着滚动声,还有凄厉的像疯了一般的人发出的笑声,还有脑袋上眼角滑落的血水!
几星期后,医院解剖组发出篇学术论文“人在割断脊椎与神经后,会控制不住地大笑,会流泪,状态可持续半小时之久!........”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