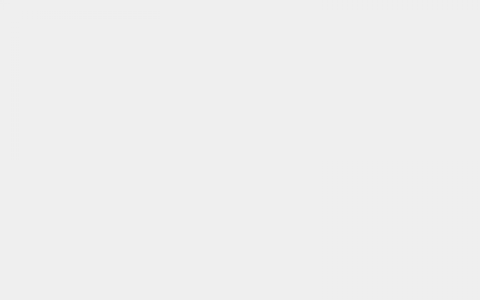你好,首先请你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这次交谈。你连死都觉得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一点你应该做得到。
看了你的来信,知道你陷入了一个恐惧症中,首先你要明白这只是一种病症,并不你想像的那么恐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你的生存环境,生活圈等等都有关。其实生命谁不留恋呢,只要是生命的个体,都会留恋生命。在死亡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苍白的,应对这句话,在圣经里就有“人活着就是来赎罪的”之说。人生因为死亡注定是个悲剧。这些东西谁人都懂得。
既然谁人都懂得,那么怎么不是每个人都恐怖生命的消逝呢?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考虑到死亡,也会害怕死亡,像你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是人,是高级动物,我们并不能傻傻的等待死亡,而是勇敢的面对它。这时先哲们就留下了有关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等一系列的名词。创造这些名词和意义就是不想让我们生活得太空虚、太空洞。相信你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也看到过,人生存着是为了寻找一个生存的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你对团体所做贡献的大小,这个意义体现在你对整个环境和集体带来的贡献。做个生活的智者,是我们唯一现实的做法。“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死亡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过程,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生死存亡的规律。死亡实际是群体对于特定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群体的延续,在于个体的不断死亡,而个体的不断出生,构成了群体的永恒存在。只有对死亡的认识升华了,我们才能正确地面对人生,超越死亡。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正确的认识生与死,作为一个21世纪的知识份子,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年轻人,怎么会躲在自己为自己织的网中,无法自拔!你该醒醒了,理清灵与肉的关系,正确选择你的人生观、生死观。我相信你能做到的,因为这并不能。
如果明明知道一件事没有选择的余地,你还在苦苦思索,那么你真的不是个智者,真的不会经营自己的人生,正常的看待这一切,享受你的人生,找到你在现实的价值。人生只是一出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出戏中的一个演员,演好自己的角色,到了谢幕时你会轻轻的说一句我该退场了。我为人类的发展进程贡献了自己的一份。不要有遗憾~
保持好一个轻松的心态,不要沉醉在一个事件中无法逃离。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单纯的恐惧症了,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
有什么事随时和我交流。记得做个生活的强者,勇者无畏嘛,呵~
给你找点资料看看《培根的论死亡》好好看看。
《培根论死亡》
面对死亡,人们充满了恐惧,就像小孩害怕在黑暗中独自行走一样,而且当小孩听到的故事越多,那么他与生俱来的恐惧也就越大,人们对于死的恐惧也是这样。当然,把死亡看做是罪孽的报应和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旅程,则是圣洁而虔诚的,而把死亡看做是向大自然进贡的祭品而感到恐惧,则是软弱的表现。然而在宗教的默想中,有时却混杂着虚荣和迷信。在某些天主教教士充满禁欲内容的书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思想的一根手指被挤压或被拶痛应该会怎样,进一步想像一下死亡将会使全身腐烂分解,这种痛苦又会怎样。
其实,死亡的痛苦根本无法和肢体上遭受刑罚的痛苦相比,这些维系生命的最重要器官并非人体最敏感的部位。所以,正如那位以哲学家和正常人身份著书立说的先哲所说的那样:
伴随着死亡所带来的痛苦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呻吟和痉挛、面目扭曲变色、亲友们的悲痛、丧服与葬礼,这些场面都显示出死亡的恐怖。
然而,人类的心灵并不是真的如此脆弱,以至不能抵御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可以召唤许多伙伴,帮助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仇恨让人可以压倒死亡,爱情让人可以蔑视死亡,荣誉使人们敢于面对死亡,哀痛的心情使人勇于面对死亡,而心灵却会在怯懦和软弱的折磨下在死亡到来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我们都知道在奥托大帝自杀之后,他的许多臣民出于对他的忠诚和同情而陪伴他一起面对死亡。此外,塞内加还补充了一个不怕死的原因:苛求和厌倦。“想想你用了多长时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别说勇敢和伤心的人会想到死亡,就是烦恼的人也会想死了。”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谈不上有什么勇气、也谈不上穷困潦倒的人,一旦他总在重复地做着同样的事情直到厌倦的话,他是宁愿去死的。
但有一点也应该明确指出。那就是说,死亡是无法征服那种伟大的灵魂的。这种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始终如一而不会失去他的本色。
奥古斯都大帝在他的弥留之际,所惟一关注的只有爱情:“永别了,里维亚,我的爱人,请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提比留斯大帝则根本不理会死亡的逼近,正如榙西佗所说:“他的体力虽然已经日渐衰弱,但是他的智慧却依然敏锐。”
菲斯帕斯能够以幽默的态度来迎接死亡的降临,他坐在椅子上说:“难道我将这样走向天堂成为神吗?”
卡尔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勇敢地对那些刺客们说:“你们杀了我吧,只要这一切对罗马人民是有利的!”随后他就从容地引颈就戮了。
塞纳留斯直到临死前所惦念的还是工作,他的遗言是:假如还需要我做些什么,那就快点拿来,我的时间不多了。”诸如此类,视死如归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可以看到,斯多葛学派的人把死亡看得非常重大,并且 ,由于他们为死亡所做的准备工作过于隆重,从而也就使死亡显得更加可怕。有人说得更加绝妙:“生命的终结是上天赋予的恩典之一。”
死和生都是自然而然的。对一个婴儿来说,或许出生是和死亡一样的痛苦。人在热切的追求中死亡,就像一个人在热血沸腾时受伤一样,当时没有感到伤痛。所以,当人们下定决心,执意向善时,是感觉不到死亡的可怕的。但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世间有最甜美的歌,还有就是当一个人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和期待时所说的那样:“成能的主啊!您现在可以遵照您的意愿,释放您的仆人安然离去了。”同样,死亡还具有一种作用,就是它能够消除尘世的种种困扰,打开荣誉和赞美的大门——“活着时遭到别人嫉妒的人,死后将会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思念。”
原载拒绝转载~
光绪死因分析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