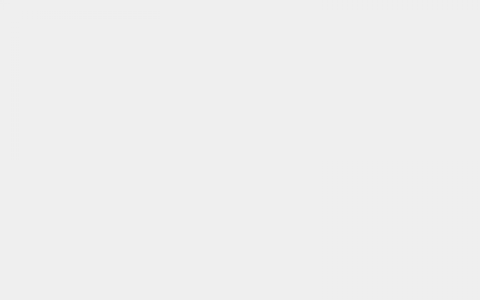根本就挂不上号。如果有关系
能挂上号
建议去这两家看。还有万和,是颈椎病专科医院,这家医院治疗效果也可以,挂号能好挂一些。
祝健康,纯原创,求采纳~
以前治疗过吗?有什么治疗的效果么,我觉得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就要微创或手术治疗了。
找个专业骨科瞧瞧吧。
山东新泰洪强医院网上可以先咨询的,或许能具体帮到你。
按照所有成功学意义上的标准去衡量蔡磊,他都是一个能够掌握话语权的人。
他曾在世界龙头地产集团担任高管,后又出任京东副总裁。他推动了中国互联网财税事业的发展,曾开出国内第一张电子发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请他做客座教授。前两年,他还结了婚,妻子是北大医学院的硕士,他们育有一个可爱的小孩。
但在他41岁这年,他确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俗称渐冻症,位列世界五大绝症之首。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疾病至今没有任何一例病人被成功治愈,无药可医。多数病人都会在3至5年内迎来生命的终结,当运动神经元凋亡到无法再支撑心肺功能的地步,他们会经历呼吸衰竭而死去。
在过去几十年的人生中,蔡磊用知识、勤奋、超乎常人的热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这一次他为自己揽下的,是个困难到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他要找到能够治愈ALS的新药。
这是一场人与死亡之间的战争,进度条只剩下几百天。他不去环游世界,数着日子熬夜工作,和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家建立联系,拿起互联网人的武器,打破既有的药物研发壁垒,链接起所有可以运用的资源。
有同样患病的朋友问他,为何不放缓些自己的脚步,“(这是)尖端难题,世界级别的,恐怕外星人才能解决”。他的回答是:“不难的事情,做起来没意思。”
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乐观背后,是一个残酷的、极有可能落败的生存故事。但此举成败,牵涉到的是几万个同样患病的家庭,蔡磊决定为自己奔走,也为成千上万人奔走。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命运正紧握在自己手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樊东升给出诊断结论时,比其他任何医生都更加斩钉截铁,他告诉蔡磊,你患上的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其他可能的疾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
蔡磊开着玩笑问他,那我就是快死了?樊东升在桌上用双手比划出一段20厘米左右的距离,他说,“你的生存期有这么长”,然后将手的距离合拢,只剩下一小截,接着说,“现在还有这么长”。
这是2019年9月,距离蔡磊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已经过去了一整年。
起初,他感受到左手手臂上的肌肉在跳,更准确点形容,是肌肉速颤,昼夜不停。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警觉,他是国内某互联网大厂的副总裁,主要负责财资方面的工作,同时期,还带着集团的4家创业公司。此前的六七年间他几乎都没有去过医院,他觉得,那太花费时间。
就这样拖上小半年,情况不见好转,直到第二年的2月,他决定去协和医院看看。神经科主任医师刘明生看了他的肌电图检查结果,并未明确给出答案,只说,你这病不太好。刘明生问他有没有时间住院,蔡磊说,目前住院是不可能有时间的,于是医生就让他回去。
“你不开点药吗?”蔡磊问。但刘明生说,不用开,回家吃点维生素B就行。当时蔡磊心中还挺高兴,心想没什么大问题。
要很久之后,他才能意识到,当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肌肉速颤的症状,就已经意味着体内的运动神经元严重凋亡,肌肉已经以几乎不可逆的趋势开始萎缩。
这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起病表征,这种俗称为“渐冻症”的罕见病,位列世界五大绝症之首,尚未发现明确的以供检测的生物标志物,误诊率极高。医生若非足够有经验,不敢轻易给出病人明确的诊断结果。
在协和医院求医无果后,蔡磊先后去不同的医院接受过多次诊断,直到他找到樊东升,住院进行了一系列完整的疾病筛查,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后,才得到了最确切、也是最糟糕的结论。并且,樊东升告诉他,ALS这种疾病,算是无药可医。
国际上唯一认可的药物是一种名为“力如太”的小药片,一盒4000元左右,可以吃一个月,据说能够延长患者3个月的存活期,但根本无法治愈ALS,也完全不能阻止运动神经元的凋亡。
这是2019年9月,蔡磊41岁,命运从此驶离正常的航道。起初,他和所有的绝症患者一样,不敢相信医生的结论,无法接受自己的命运,此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都严重失眠,就算入睡,也会反复醒来。
算命先生说他八字中五行缺金缺水,所以受此劫难,先生点化他,让他改名蔡润谦。风水大师也算上一卦,让他搬离了原本的家。他曾尝试朋友们推荐的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治疗,注射昂贵的进口药,高烧上39度。或者去嵩山少林寺拜访点穴大师,天天做经络推拿。
但一种不甘的情绪也同时出现。
他起初不愿意和其他病患做朋友,不想将自己纳为边缘群体的一员,他心里琢磨的是,“我蔡磊,我还得干大事”。曾经,他和别人竞争做业务的时候,会对人家说,你不要做,你做不过我。对方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要命,我蔡磊不要命,你拼不过我”。
如今,换做死亡这个竞争对手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在不安之余,他的狂妄与不甘,以及被他自己形容为“疯狂”的热情,又再次被激发出来。
确诊后,他找来国内外所有关于ALS的学术论文,达1000多篇,逐篇逐句阅读。为了提高阅读速度,他找到了趁手的工具。就这样看了好几个月,连犄角旮旯里的信息也不放过,试图从中找到可以救命的方法。
2019年11月,确诊两个月后,他着手搭建成立北京爱斯康医疗 科技 有限公司。20年的工作经验形成的惯性拉扯着他,让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做出了决定,要以医疗 科技 公司为阵地,为攻克ALS找到真正有效的药物。
妻子段睿想让他放下一切工作,去游山玩水,多陪陪家人,但他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蔡磊说他只相信自己,只有自己才有可能救自己的命。在他和死亡之间,一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打响。
他估算着,如果自己剩下的时间还有三年,要是能在两年半以内找到新药,他就能赢。
首先,来认识一下敌人,ALS。
作为国内该领域资质最深的专家,樊东升是在偶然的情形下开始同这种疾病打交道的。
世纪之初,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全国做颈椎病治疗最好的医院,但有个奇怪的现象是,一些被诊断为颈椎病的患者在做完手术以后,病情仍然无法缓解。手术流程没有问题,但这类患者的情况却还有可能持续恶化。后来他们才发现,这类患者得的并非颈椎病,而是罕见病ALS。
当时,正是樊东升攻读研究生期间,在确定论文选题时,骨科教授从临床角度给他提出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如何判断这个病很可能是你们的病(ALS),而不是我们的病(颈椎病)?”
尽早作出鉴别,才能避免骨科医生错误地给患者实施手术,颈椎病手术不仅会延误ALS的诊断,甚至可能加速病情的发展。
因此,整个研究生期间,樊东升最主要的课题就是鉴别ALS,后来他发现,通过肌电图检测等手段,能够有效地将二者区分开来,检测准确性能达到98%以上。
但当时,国内对于这种疾病的认识极其有限,直至今日,能够准确地诊断ALS的医生,仍是寥寥无几。
它的确太过未知,也过于复杂。在英国,ALS更常被称作运动神经元病,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运动神经元凋亡导致的疾病。运动神经元病有一个广义的疾病谱系,囊括了平山病和肯尼迪病、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狭义运动神经元病三种类型。而狭义运动神经元病,又有好几种不同的分型。
蔡磊的左手、左臂、肩部、背部等肌肉如今已经严重萎缩,他的左臂只能无力地悬垂在身体一侧,手背浮肿着,看不出关节的纹理。而右手肌肉也渐渐开始了同样的萎缩进程。接受采访的中途,他还需要戴上呼吸机,以降低心肺负担。
他已经不再穿带鞋带的鞋子,不再穿西装和需要系皮带的裤子,发消息常发语音,或者用语音转写成文字。有次他受邀出席一场会议,落座后,想请隔壁座的女士帮他拧开矿泉水的瓶盖,对方却误以为是蔡磊“欺负”自己,他只好向人家赔礼解释说,“抱歉,我手不好”。
生于1960年的舒白患上的是ALS最经典的一种分型。2018年,她左臂起病,2019年5月,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2020年11月,她还能走路,但就在那时候,摔了一跤,从此再也站不起来。
如今,舒白只能坐在轮椅上,她可以自己用勺子进食,但已经丧失了除此以外的其他自理能力。丈夫和保姆共同照顾她,夜里睡觉,舒白要靠他们为自己翻一次身。接受采访的全程,她都必须戴着呼吸机供氧。
病友里还有病情进展更加凶猛的。王瑾的丈夫今年40岁,从2020年7月发病至今仅仅过了一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呼吸问题。还有位38岁的企业家,发病9个月,已经四肢瘫痪、生命垂危,前段时间的某天夜里,他的血氧饱和度一度降到92%,无法进行自主呼吸。
人体的肌肉由神经元支配,当神经元开始凋亡,肌肉无法再运动,很快就会萎缩。在3到5年时间内,病程发展到后期,人的身体会变得像一支融化的蜡烛,心肺功能无法得到肌肉的支持,必须将气管切开,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如若不然,则会呼吸衰竭而死。
在蔡磊建立的多个微信群内,已经有数千名ALS患者聚集到一起,他们每天都在见证死亡的发生。有时候,群内会有病友亲属告知亲人的死讯,或者,当有人开始转卖呼吸机时,就意味着,又一个人从世界上消失了。
2003年前后,由樊东升所在的北医三院牵头,成立了专门研究ALS的多中心协作组,最初共有4家医院参与协作,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家医院参与其中。他们也正在推动ALS的新药研发,但这条道路仍然十分艰险。
美国细胞治疗公司BrainStorm从2001年开始就致力于通过NurOwn干细胞疗法 探索 治愈ALS的途径,他们曾是最受患者期待的公司,且研发的药物通过了一期与二期临床试验,但就在2020年,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束,实验数据却未能显示出统计学差异,这意味着药物对ALS没有明显疗效。长达19年的干细胞药物研发宣告失败。
蔡磊记得很清楚,当天,BrainStorm股价暴跌70%,对于许多ALS患者而言,生存的希望就那样像关灯一样迅速地破灭了,“那一个星期,就死了不少病友”,蔡磊说。
20年前,樊东升团队找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帮忙设计了一套量表,以此为标准,不断收集ALS患者的样本数据。樊东升明白,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罕见病,收集数据几乎可以算作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想要建立更加完整的数据库,他们必须每三个月对患者进行一次面访或者电话随访,以更新病人的病情进程以及用药效果。这项工作耗时费力,且经费不足,樊东升只能让学生来帮忙做,付给他们劳务费用。
在20年的坚持之下,他们几乎收集到了全世界体量最大的ALS样本数据。但樊东升也逐渐意识到,这套量表不甚精密。而且,三个月一次的随访频率,并不便于及时观察患者的变化情况。
蔡磊的出现,带来了一柄极为重要的、足以突破瓶颈的利器,即,互联网。
自称“互联网老兵”的蔡磊,在四处寻医问药无果后,产生了强烈的疑惑,为何大多数医院都没有自己的患者数据库?医院与医院之间,信息互不流通,罕见病病例又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疾病研究和新药研发?
他几乎本能地意识到,大数据库的建立,是解开ALS疾病密码的钥匙。2019年11月的那次创业,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北京爱斯康医疗 科技 有限公司,他成立了一个名为“渐愈互助之家”的信息聚合平台,所有ALS患者,均可通过这个平台,自主上传完整的病情信息,并且能够实时更新用药效果和病程进展。
当时,蔡磊想要建立的数据库,不仅要考虑各种选项存在的可能性,还要能够横向打通,与医保中心的标准相衔接,以契合更加长远的诊疗规划。樊东升为他提供了一份量表,但那份材料更多要求医生协助患者进行测评,而蔡磊想要的,是患者自己或者由家属协助就可以进行自评自测的指标。
恰好,他的妻子段睿是从北大药学专业本硕连读毕业,在这个数据平台成立早期,段睿一起支持蔡磊团队共同完成指标的制定。
蔡磊告诉南风窗:“任何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一两天甚至一个星期都讨论不完,非常庞大复杂,特别难,总共做出了2000多个字段,每个字段都无比艰难。”
比如,他们想找到ALS发病原因和患者职业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设计出详细的职业选项,若是只给出“运动员”的字段,那太过简略了,要细化到足球、乒乓球、篮球等各个不同的方面。
再比如,涉及到“颈部压痛”等较为专业的数据,患者自己无法测量,他们就想办法将问题设置成“你的手可以举到什么位置”“你能坚持几秒钟”。
与此类似,不能问“用药后是否增加了排便量”,而要换成“吃了药以后,排便多少次”。
舒白说,这份量表她填写了好几天,她的双手已经几乎不能活动,只有一个大拇指可以用。但好在,设计量表的蔡磊本身就是患者,他将量表填报的方式简化为打勾和画圈,并且安排了同事去做平台的管家,直接帮助那些无法顺利上传资料的患者录入数据。
目前,这个建立不久的数据平台,样本量已经超过2000份。
作为跟患者接触最为密集的临床医生,樊东升向南风窗分析了这个数据平台将对ALS研究产生的重要意义。
“大数据平台能够实时地反映出病人的变化情况,可能我们很快就能看懂,某个药是否有效,对于一些平台的新药研发,它可以大幅缩减时间成本,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把时间缩短以后,对新药研究的投资就会加快。”
其实,在蔡磊的世界里,“万物皆可互联”的观念不只是应用到工作中,也早已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了。
2020年3月,他给段睿找来好几个线上收纳APP,建议她把所有家庭物品拍照上传至“系统”,给每个柜子编码,形成系统中的文件夹,然后将物品图片拖进文件夹内,做好保质期限的备注,“就不会找不到东西了,关键是防止过期”。
段睿觉得蔡磊特别好笑,于是发了条朋友圈,写道:“下次我可以骄傲地同客户讲,我家的后台运营已经初步实现物联网管理了。”
作为妻子的段睿,可以算是将蔡磊的策略看得最清楚的人。
她是药学专业的“圈内人士”,比寻常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蔡磊想要推动罕见病新药研发的艰巨性。
“他这个事情就是难到我们圈内人都是不敢想的,都认为这个思路是没有这条选项的,因为首先你研发需要很多资金,需要一个团队,需要很多年,但失败率非常高,它不是以个人之力能够推得动的。”
BrainStorm研究了19年都攻克失败的ALS,就凭蔡磊,如何成事?但段睿知道,对于蔡磊而言,“互联网”绝不只是一柄利器,更是一套决策的底层逻辑。如果按部就班走原有的新药研发流程,败局毫无悬念,但蔡磊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旧有的 游戏 规则。
与新药研发相关,最主要会涉及到投资者、医院、药企、科研团队、病患、注册部门,任何环节,缺一不可。但对于ALS的新药研发来讲,几乎每个部分都存在缺乏,这也符合常理,是罕见病药物研发的痼疾。
投资者不愿意将资金注入ALS这块狭小的市场,因为看起来显然没得赚,相较之下,他们更愿意把钱投给同属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诸如阿尔茨海默症,因为患病群体庞大,回报率高。
他细细地给对方算账,阿尔茨海默症纵使有1000万病患,但并没有多少患者会为这个疾病付费,因为患病者年迈,自己不认为得了病,也不愿意儿女在自己身上多花钱。
“你不是说阿尔茨海默症1000万人吗?有几个是你的真实客户?我的姥爷现在82岁,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他不会花一分钱治这个病,你拽都拽不过去。”
而他认为,ALS的患病群体年龄大都在40到60岁之间,是家庭和 社会 的中坚力量,且夫妻只要一方患病,另一方定然会被同时卷入,照料伴侣的饮食起居,无法再正常工作。因此,他告诉那些投资人,一个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会花上几十上百万救治ALS患者,因为一个人垮掉,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垮掉。
“ALS每年新增2.6万人,我就按现存10万人来算,每个人愿意花100万去治,就是1000个亿啊。”
他同时将自己已经掌握的几千人病友群以及逐步完善的患者大数据作为谈判的筹码,告诉投资者,你都不用推广,消费者的市场,我直接对接给你。
于是,100多位投资者中,最终也有一两位被游说成功,同意支持ALS的新药研发。
而樊东升认为,ALS仍然是值得投资的研究项目,因为,ALS与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常见病同属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们的发病机理相似,而ALS是其中病程发展最快的疾病。从资本角度来讲,ALS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研究模型,若是研发出对ALS有效的新药,很可能就直接打通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通路。
蔡磊深谙这一点。2021年年初,他就顺利说动原本致力于研究阿尔茨海默症的陈功教授开始转向ALS研究。
陈功于2019年辞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席位,返回国内,加入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为解决重大脑疾病进行神经再生方面的研究。
2013年,他所在的团队,就用一个神经转录因子将老年痴呆症小鼠脑中的胶质细胞成功再生为神经元,在国际上是首例。
神经元再生技术若发展成熟,则包括ALS在内的一系列神经退行性疾病都能被攻克。
用段睿的话来说,这就好比扫雷,“就是你点开一个空去,‘哗’一下全开的那种感觉,啥都能治,只是对这个效果更好,对那个效果差一点,这种感觉是很痛快的”。
在蔡磊的链接下,包括陈功教授、清华大学鲁白教授等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都与从事临床的樊东升建立了联系。
原本,完整地走完新药研发的全流程大概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在各种资源被充分聚合的情况下,陈功告诉南风窗,这个进程最快能加速两年。而诸如陈功的研究,前期在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年的实验,如今,在蔡磊的推动下,有望在明年取得初步成果。
1978年,蔡磊出生于河南商丘一个贫苦的军人家庭,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上初中,后来父亲早逝,家庭负担沉重,他总想凡事比别人做得更好些。考试要拿第一,打 游戏 要比别人好,就算体格较小,但只要有地痞流氓敢欺负他,他一定跟对方大干一架。
“我知道自己干不过他,但是你敢挑衅我,我就敢跟你干。从来不服输,我就这样的一个人。”
(文中段睿、舒白、王瑾为化名)
编辑 | 李少威
新媒体编辑 | 煎 妮
排版 | 文 月
月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