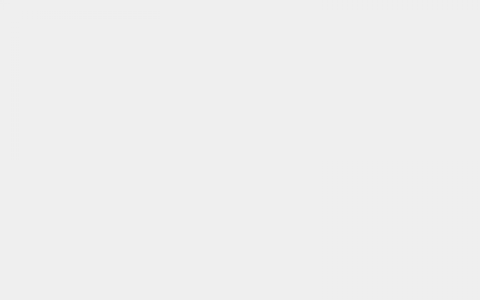阿荣:14岁开始吸毒阿荣今年15岁,外表似乎和同龄人没有多大差别:未经梳理的短发,害羞的表情,在陌生人面前有意压低的嗓音——如果呆在学校的话,他应该才读初二。
阿荣不爱读书,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同龄人大多还呆在学校里,所以他平时都是和比自己大的玩。玩得最要好的几个二十五六岁的朋友,大都是吸毒者。那些人在一起打麻将时,经常会轮流注射毒ping。阿荣回忆,去年五六月的时候,一个叫阿飞的朋友邀请他也“搞一针”,刚开始他没有同意。连续几天去找朋友玩,阿飞都向他发出邀请。后来,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他决定试一次。朋友们很热情地张罗起来,用绳子帮阿荣扎好左手腕,让手背的青筋凸出来,然后用注射器把稀释好的海洛因吸进针筒,交给阿荣。 大约10分钟后,毒品发作了,阿荣只感到昏昏沉沉,便到房间里的床铺上躺下睡觉。两三个钟头之后,他才醒了过来。
此后,阿飞经常打电话问他:“还要吗?”为了和这些比自己大的朋友打成一片,他没有拒绝。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这样,阿荣迅速成了一个“瘾君子”。当他主动开口讨要毒品时,朋友们开始向他收钱了,一般50元一次。 “原来他们只是想赚我的钱而已。
阿荣此时已陷入毒品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每天至少要注射一次。 阿荣的父亲在柳江县基隆开发区做建材生意,他帮父亲干活每个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但这些钱只能维持几天的吸毒开支,他只好向父亲要。父亲知道他拿钱去吸毒后,除了责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多是要钱的时候不给罢了。阿荣就会趁父亲不在家时,把自家门面的铝合金等建材偷卖给附近的同行,钱到手就立即跑去找朋友买毒品。去年8月的一天,阿荣到姐姐家玩,又躺在床上吸毒,民警闻讯赶来,送他去强制戒毒。本来阿荣半年前就可以离开戒毒所回家了,但家人要求他在里面呆够一年,阿荣说自己也同意。我不愿回家,我怕再见到那帮朋友。据戒毒所民警介绍,出去后复吸的起码在80%以上,因为一回到以前的环境,人很难摆脱其他吸毒者的影响。像阿荣这样的未成年人,意志更薄弱,更容易复吸。
阿兵是澄海外砂人,因年幼其母病亡,其父忙于生计无暇照管他,自7岁起,阿兵模仿大人们抽烟,并以之为荣。他说,每天放学后燃起一根香烟吞云吐雾,走在同学们中间感觉特有面子。14岁那年,勉勉强强读至初一的阿兵干脆辍学了,终日跟在乡里几位“大哥”身前身后当起了小兄弟。去年初,他结识了乡里一做餐饮生意的“大哥”,几番来往后,阿兵很得大哥喜欢。慢慢地,阿兵也发现了大哥原来是“白药仔”,但他也不以之为忤,相反还认为这是“酷”的表现。去年中,趁大哥不在家,小兵偷了一点“白粉”终于“开禁”尝了新,并从此成了一名“小道友”。吸上白药后,因无钱买药,小兵便在一“道友”“教授”下当起了“鱼虾蟹”庄家,以赌钱为营生。据称,那些“鱼虾蟹”的骰子都是用磁铁做了手脚,因此聚赌时基本都是赢钱,有时一天纯收入达三四百元。小兵称其每天下午常在陈厝合、辛厝寮一带“开局”,赚了“工资”后便买“药”过瘾。今年2月19日,小兵被警方抓获,在审讯时因药瘾发作口吐白沫,结果被送强制戒毒。39岁的周挺(化名)一头白发,他说自己进戒毒所之前就是这样了,不知满头白发是不是和自己17年的吸毒史有关。周挺的爸妈是西安一所高校的老师,从小他就生活在书卷气息颇浓的大学家属院,20岁的时候,周挺大学毕业,留在了父母所在高校,做后勤工作。
“后来想再学点儿东西,就去学驾驶,在驾校认识了一个大我六七岁的哥们儿,他经常招呼我去他家玩,有一次去他家,看见他和他女朋友在吸海洛因,于是我就特别好奇,他说来一口吧,我就这样被拉了进去。”周挺说,“就这样一直吸了17年,直到去年来到强制戒毒所。”
周挺说,因为吸毒,每月7000多元的收入,用在毒品上的却有6000多块钱,生活上大多时候只能靠父母和家人照顾。“父母知道我吸毒,他们很伤心,毕竟是做教育工作的,自己的儿子却接触毒品,他们也一直劝我,但是却没有用。”他说,“来到戒毒所后,民警经常让我们静坐反思,这个过程带给我的启示其实挺多的,心里也渐渐开始对吸毒这个行为有了抵触,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爸妈说,他们还给我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亲对象。” 周挺的父母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说,自己本来是有一个幸福家庭的,但是因为吸毒,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尤其是亲戚看他的眼神,这让他很难承受。
周挺说,除了避免接触那些吸毒者的圈子,戒掉心魔很重要,而且回归社会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包容的态度,“有了新的朋友和新的圈子,生活就会重新开始,我希望,离开这里之后,我的生活会是崭新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