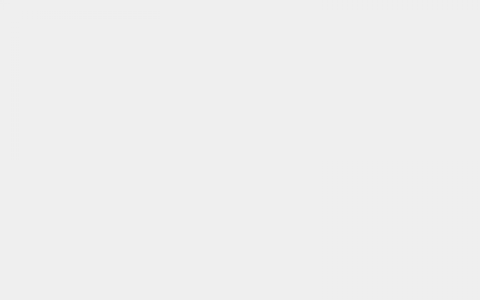本名:钟阿城。
阿城80年代以《棋王》、《树王》、《孩子王》起始,到《遍地风流》止,尔后就销声匿迹了。直到1998年书市上摊出《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跟着是由《收获》专栏文字结集而成的《常识与通识》,再就是旧作新版的《棋王》、《遍地风流》,阿城算是复活了。
阿城的作品评价
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
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0年代后定居美国,仍有不少杂感和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
你好:阿城为阿勒楚喀的简称。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市辖区,位于哈尔滨市中心城区东南23公里处,城区于1994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版画之乡”。阿城在金朝的全称叫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东南)4公里许(白城),是金朝第一个都城, 金朝共三个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东南)是金朝第一个都城,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都;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为金朝第二个都城,称金中都;金朝第八位皇帝宣宗完颜珣于1214年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 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于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建都立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 并于1125年灭辽朝,两年后,再灭北宋。阿城《棋王》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出生于北京 。
中学未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去山西农村插队,此时开始习画。为到草原写生,转往内蒙,而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时,与著名画家范曾结识,两人超过“代沟”而成莫逆之交。
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处女作《棋王》一发,便震惊文坛,先后获 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全国秀中篇小说奖。后有《孩子王》、《树王》等作品。
一、棋王
阿城是一个在创作中对中国文化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是不会有出息的。”“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同世界对不起话的。”他还说:“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浸出丰厚的中国文化。”阿城不但在理论上强调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更注意文化本源的追寻与思考,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重的中国文化氛围。小说《棋王》就是“文化寻根”的代表作。
在《棋王》中,阿城主要通过对“棋呆子”王一生在“文革”时期的人生经历的叙述,展现了王一生的人生见解和精神特质。作为城市平民的后代,王一生从小就体会到社会的艰辛和人生的困苦。他以彻底的逆来顺受和无欲无求来适应艰苦而无望的生活,并达到了一种超乎世俗的个体精神的审美的境界。吃食、棋艺和交游自然,构成了他内在生命与精神的充分的自足与自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任何奢望,唯一能够使他获得乐趣、忘却尘世烦恼的,只有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
下棋——精神的饥饿
王一生出生在贫寒之家,而且父母都没有文化,尽管王一生脑筋好,老师都喜欢,可贫穷夺去了他的一切娱乐,学校春游、看电影他都不去,为的是给家里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文化大革命文化本身的凋敝还不如“呆在棋里舒服”。
醉心于一种技艺而至于迷、而至于呆,除了可敬的一面,更多的是叫人可怜。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能够学什么本事呢?
幸运的是偶然的机遇——“车轮大战”——一举成名。
吃——肉体的饥饿
王一生家里非常穷,虽然嗜棋如命,却连一副棋都买不起,他的母亲用捡来的废牙刷柄磨了一副无字棋算是给他的一份遗产。别的青年视下放插队为畏途,他却以每月能得到42斤粮票、20几元钱为极大满足。这样的家庭背景必然使他对饥饿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他自己吃饭时连一粒米一片油花都不漏掉的。这又何止王一生一人!
二、棋王的深层结构
《棋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目击者,由于目击者处于故事的边缘,它的角度是充当主要人物和事件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因此从表层结构来看他并不是处于事件中心的主人公,而只是王一生的亲密朋友。
“我”最初认识王一生时对他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对他的怪异产生了困惑,这种叙述视角使读者随着“我”对棋王的进一步描述而进入到故事文本中的探寻,于是随着文本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作者运用目击者“我”与棋王不同之处的逐渐消弥和价值取向的趋同,展现出来的却是“我”从“迷”(寻道)到“悟”(悟道)这一过程的深层结构与意义,使在表层结构中处于故事边缘的“目击者”成为深层结构中真正的主角。
开篇是阿城苦心经营的神来之笔,火车快要离站,整车的知青都在与亲友哭泣告别,只有“我”和王一生独坐在车厢里,表面的相同却正好显示出态度的不同,“我”是因为走资派的父母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无人相送,于是叙述中的反讽基调暗示了“我”对时局的强烈憎恨和否定,并在人生困境之中开始消极而迷惘地寻找人生的意义: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王一生却没有挥泪告别,因为他对插队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而且还在纷乱之中邀请“我”与之下棋,因此在“我”的眼中,王一生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并以他对吃的独特见解和高超的棋艺引起“我”的同情、理解直至喜欢,但这只是“我”寻道的开始,此时并未真正地了解王一生,因此始终是用调侃和揶揄的反语来表现“我”对他的不认同。
如在火车上听到的王一生这个棋呆子不解人事、有违时尚的呆人呆事;王一生所讲的老掉牙的“节约粮食”的故事;以及对“我”如何混吃的细节打探等等,尤其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进行的细微地描写: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
此后故事的进展仍以“我”同王一生之间的联系而展开。分手几个月后的一天,王一生来访,当“我”和王一生谈起现状时,“我”同意王一生“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的看法,可又心有不甘,“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在这儿,“我”明白地告诉读者:“我”一直在思考探索“活着”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独自思索,没有结果,而当王一生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总是以他精神上的通达和更有境界的处世之道给“我”以极大的启发。例如当倪斌出场时,“我”的叙述就传神地写出他
的种种可笑之处:在知青场那种“广阔天地”里还保持着极不和谐的文雅举止,在吃蛇肉时还大谈其父的名士风度,这种叙述的口吻暗示着“我”(或者说“我们”)对倪斌的嘲笑,当倪斌把自己珍藏的食品“贡献”出来让王一生和众知青们共享后,大家还想去翻点出来,王一生却说:“不要闹,人家的是人家的,从来农场存到现在,说明人家会过日子……。”显示出“我”(我们)与王一生境界的不同,而后,为了让王一生参加地区象棋比赛,倪斌不惜用祖传的古董打通“关节”的行动的确证明了王一生当初对他的评价:“倪斌是个好人。”
在农场中,王一生曾向“我”谈起他轻易不向外人道的、令人心酸的母亲和家庭。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从小体会到生活艰辛的王一生直觉地认识到“生命”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他牢记母亲的话:“你在棋上怎么出息,到底不是饭碗。”因此对于“吃”格外的虔诚和精细,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但“生不可太胜”,正如那位运棋如神的老者,他以拣垃圾为生,“为棋不为生”的祖训使之在最低下的社会地位上保持着最自由的心灵,王一生对棋道的顿悟正是师法于这位以拣破烂为生的老者,并从他身上得到启示,决意摒弃物质生活的困扰,自觉地从下棋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
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王一生则在意识和行动上自觉地完成了“雅”与“俗的自然统一。因此,当他下乡插队不愁一日三餐时,便请假外出满山遍野去会天下“异人”。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正是“我”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所力图找寻的精神支柱。此后,随着对王一生的了解,“我”的叙述语气已经完全由原来的调侃变成了
庄重与温和,并开始理解了王一生对“吃”的态度和观点,而后“我”和知青们筹划安排的一盘蛇肉会餐则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肯定和模仿,其中对细节的操作和全心的投入直至把蛇骨吃得“一个渣都不剩”,无疑是“我”对于“吃”的重要性的首肯与实践。特别是王一生走时“我”对他可称是“情深意长”的叮嘱等等,在这一系列情节中,作家无意中传达了“我”与王一生不同寻常的亲密,“我”在火车上对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太认同已是烟消云散,好像两人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默契与缘份,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内在投合使王一生的故事发展成为“我”悟道的旅程。
小说的结尾,在王一生的象棋大战中“我”始终是最关注他的人,而他的“瘦小黑魂”形象在定格的瞬间也终于使我找到了寻觅已久的人生意义: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因此当王一生的故事结束时,小说并未因此而结束,作家节外生枝地在最后一段中又写道:
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小说中的“我”顿悟人生哲理的同时,读者也随之能够体会到《棋王》在讲述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这一表层结构下隐含着一个深层结构:“我”面对惨痛的人生经历和恶劣的外部环境对“活着”这一问题的不懈追索,并由于受王一生的影响和启示最终找到答案的全过程,小说最后我“拥了幕布,沉沉睡去”,这是“理得”后的“心安”。
综观小说全文,以“我”的出现开始,又以我的睡去作结,它告诉我们:小说中除了王一生的故事,还有一个“我”的故事,正如阿城自己所说:“《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王一生和叙事
者是两个元,最后这个主观叙事者‘我’,他是悟到了。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了……”。这种“我”的主观世界正是文本的深层结构,而在表层结构中处于故事边缘的“我”正是深层结构中真正的主角,并随着主人公故事的进展而追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这种小说中潜在主角、深层结构的存在并未颠覆显在主角与表层结构,而是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加了作品魅力,使《棋王》具有更为深远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