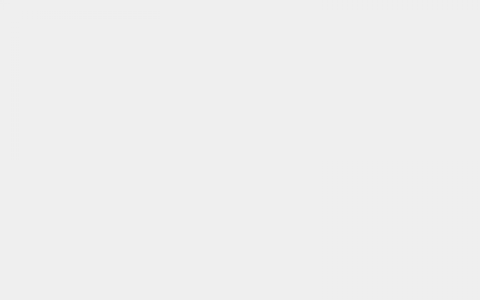孙益红
1966年10月出生,江苏省建湖县人。1994年获原上海医科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1998年晋升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副教授,2002年起担任普外科副主任,2003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擅长普通外科各类疾病的诊断和规范化手术治疗工作,尤其是对胃癌、大肠癌等消化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专业译文20余万字,参与编写学术专著两部。获上海市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2项。2012年被评为中国名医百强榜百强名医。目前担任中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胃肠外科学组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胃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创伤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消化外科》杂志特邀编委 。
秦新裕
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目前担任中山医院党委书记,2000年被学校确定为外科学科带头人。秦新裕医师197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81年上海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上海欧美同学会理事兼医务分会副会长,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药物评审委员。 他还担任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和中国临床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外科杂志、中华普通外科杂志、中华消化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中华消化外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外科理论与实践杂志、岭南现代临床外科杂志、临床外科杂志、外科年鉴(Annual of Surgery)中文版等杂志编委。共发表论文220余篇。曾主编《外科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参编《实用外科学》、《现代外科学》、《胃肠外科学》、《胃肠动力学》等著作。 秦新裕医师曾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次、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各1次。1998年被列为上海市百名跨世纪医学科技人才。主要从事普外科、胃肠外科、胰岛移植、手术后胃肠动力紊乱的研究,擅长胃肠道肿瘤和各种外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目前负责的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上海市科委重大课题2项、上海市百人计划课题1项等 。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原名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它诞生于1835年,由美国传教士伯驾(Dr.ParKer)先生创办,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西医院;1886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遂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2001年10月,原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中山大学,医院更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中山二院),分南北两个院区,院本部位于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占地面积32150平米。
在这片中国西方医学的发源地,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周寿恺、毛文书、秦光煜、林树模、钟世藩等一大批勇于创新、默默耕耘的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中国首例膀胱取石术,首例病理解剖术,首例眼疾手术,首张医学X光片,第一个医学留学生和第一个女医学生,第一本医学杂志等,都在这里诞生。
历经172个春秋,医院已经建设和发展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拥有MRI、CT、ECT、DSA、彩色多普勒超声 仪、碎石机、骨密度仪、自动化分析仪、直线加速器、热疗隐形超声刀、高压氧等一大批现代化设备,下设内科(心血管、内分泌、消化、呼吸、血液、泌尿、风湿)、外科(普外、泌尿外、心胸外、骨外、神经外、烧伤整形外、小儿外)、妇产科(生殖内分泌、肿瘤、围产)、儿科(血液、新生儿、呼吸)、耳鼻喉科(耳、鼻、喉)、口腔科(颌面外、修复、口内)、眼科、皮肤科、中医科、急诊科、综合科、监护科(ICU、CCU)、神经内科、康复科、肿瘤科、麻醉科、放射科(放射影像、放射介入)、检验科、超声科、核医学科、病理科、输血科、药剂科、预防保健科、手术室、供应室、医学研究中心、博济医疗中心等数十个临床和辅助科室。其中一级专业科室16个,二级专业科室27个,医技科室12个,拥有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授予点12个,硕士授予点27个,其中内分泌内科、妇产科、儿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口腔科为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学科,心血管内科、普通外科、骨外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为医院重点专科。
1949年医院展开床位仅195张,日门诊量不足220人次,1958年床位增至500多张,日均门诊量1500人次以上;1984年医院职工1000多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28人;2005年全院职工1332人,其中教授49人,副教授135人,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11个,博士导师19人,硕士点27个,硕士导师100多人。2006年,全院开放床位1380张,年门急诊量130多万人次,年出院病人3万多人次。南院区(广州市海珠区盈丰路33号)于2002年开业,全力创办以普通外科为特色的大专科、小综合院区,打造华南地区肝胆外科特色品牌。
近几年,医院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2002年,小儿血液科中国第一株人胚胎造血干细胞系建系成功;普外科宋尔卫博士与哈佛大学医学科学家合作 ,应用RNA干预抑制病毒感染的研究论文发表于2002年7月《自然·医学》 (Nature Medicine)杂志,并被美国《科学》杂志评选为“2003年度世界十大 科技进展”代表性成果;消化内科《自主免疫状态下乙肝病毒变异的规律》课 题参与国家973计划;小儿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系列研 究》、内分泌内科《关于瘦素的系列研究》分别获2003年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 奖、二等奖;2004年度儿科《提高儿童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实验与临床研究》 、妇产科《保存卵巢功能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内分泌内科《糖尿病足的预警和综合防治研究》分别获取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
多年来,医院为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一系列荣誉:连续被评为“广东省文明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广东省白求恩式先进集体”,2003年获全国、省、市三级抗非模范(先进)单位。医院秉承南北院区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学科群为主体重新布局,实现一个医院、两个院区、各具特色,统一品牌管理,将优良传统和文化在两个院区发扬光大,实现成为一所国内知名、国际有一定影响的强大的现代化综合性教学医院的战略目标。
周边公交:(南方大厦站)旅游2线 夜1 夜31
鲁迅的牙病虽然有遗传的原因,但他个人的饮食习惯也对此极有影响。鲁迅是非常热爱甜食的,比如在日本期间吃的羊羹,是一种豆沙类的甜食,到北京后,半夜“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到上海后还经常自己去买糖,所以沈兼士回忆鲁迅嗜好之一就是爱吃甜食:“先生则最喜欢吃糖。吃饭的时候,固然是先找糖或者甜的东西吃,就是他的衣袋里也不断装着糖果,随时嚼吃。”
甜食对牙齿的腐蚀程度是很大的,鲁迅在牙科诊所看牙时,好几次就是修补蛀牙,牙病的严重导致鲁迅在1930年就不得不拔去余下真牙,过上了戴义齿的生活,这必然导致咀嚼能力的退化。牙齿咀嚼食物不力,未粉碎的食物到达胃部,会增加胃部的负担。
鲁迅的胃在少年时已经因吃辣椒落下病根,而他饮食习惯的另外方面又使这一情况雪上加霜,他爱吃硬的东西、油炸食品、腌制类食物以及夏天吃冰,这一切无不会加重对胃部的摧残,所以鲁迅最后两年大病时,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就是胃无法消化食物所致。
须藤在回忆文章中下论断:“胃肠病最易罹营养不良,而于生成孱弱的体质尤易招患,结局酿成结核性的体质。”
甚至认为胃病还应该为鲁迅的肺结核负责。无论如何,鲁迅的饮食习惯与他的常年顽疾牙病、胃病息息相关,这看上去不起眼的普通日常病,在鲁迅重病的时候却成为千里之堤崩溃时的蚁穴。
须藤五百三的医术及处理方式须藤五百三曾在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学习,取得医师执照后任陆军三等军医,在朝鲜任过道立医院院长,后来到上海开设须藤医院。
从鲁迅日记可看出,鲁迅早期是经常到篠崎医院及福民医院看诊,这两间分别是上海最早和最大的日侨综合医院,但1932年鲁迅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须藤,从1933年鲁迅请须藤为海婴诊治起,其后3年,鲁迅几乎只找须藤看病,须藤简直成为了鲁迅的私人医生。这样重要的医生,他的医术如何?
从须藤医治鲁迅的过程来看,他的医术值得商榷。1934年7月,鲁迅去医院看病,从后来的病症发展观察,鲁迅肋痛、发热、后期背痛,当时是患了肋膜炎。须藤一开始诊断为胃病,后来说是受寒着凉,最后说是西班牙流感,这些都是误诊,因为诊断错误,不能对症下药,鲁迅在1934年底连续发热了1个多月,生生拖垮了他的身体,肋膜炎也没有断根。
1934年成为鲁迅 健康 的分水岭,这次大病之后,鲁迅明显衰弱下来,每个月都要生病,身体无力,抵抗力差,以至于后来一受寒就容易酿成重病。1936年5月,鲁迅又发热,须藤一开始诊断为胃病,鲁迅躺了10天,“医生还没有查出发热的原因”,须藤继续治疗,越治越糟糕,终于在许广平及冯雪峰的请求下,请了美国的邓医生前来诊治,再加上X光胸片检测,发现鲁迅为肺结核及肋膜炎。正是因为有了正确诊断,须藤才开始有了诊治方向,为鲁迅注射抗结核剂,抽去肋膜间积水,由此鲁迅的病才慢慢好转。
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医生及X光片的指引,须藤可能还在以治疗胃病的方式治疗鲁迅,鲁迅是否能撑到10月还很难说。
在鲁迅的死因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何权瀛依据1984年上海各大医院对鲁迅1936年X片的会诊,认为10月17日鲁迅着凉后,左侧严重肺大泡破裂后引起的左侧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是病人致死的直接原因,但须藤当时将鲁迅的疾病误为心源性哮喘进行医治,没有进行抽气,这个医疗失误导致了鲁迅的死亡。
如此看来,须藤的医术水平十分堪忧。除了医术之外,须藤在对病人的处理上也有问题。他未考虑病人身体情况,轻率地建议身体虚弱的年老病人长途远行。鲁迅6月病重到无法起身,经X光显示为肋膜炎和肺结核,大约治疗了10天左右,须藤就劝鲁迅出国疗养,鲁迅接受了建议并开始认真打算,每过十天半个月都设定一个目的地,还仔细考虑了同行人员。
8月1日鲁迅仍在发热,肋膜炎还没好,胸腔有积水,体重只有76斤,但须藤表示肺病已经好了,肋膜炎不足为意,准许鲁迅可以随意离开上海,鲁迅因此又积极考虑出行事宜,直到8月31日他才意识到自己无法出去疗养。作为医生,须藤一直向鲁迅传递他所生的病并不严重的信息,鲁迅7月6日给母亲写信说:“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事实是鲁迅一直到10月还在发热。
须藤告知鲁迅“肺结核对于青年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是并不致命的”,新瘘 黄源也听到须藤跟鲁迅说:“现在肺部很好,还可以活十年。那时少爷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过分担心了。”
而当鲁迅痰中见血,吐血数十口时,须藤跟他说跟病灶无关,“于肺无害”,鲁迅一直发热,须藤说肋膜炎不足虑,抽完水就好了。
医生将病状情况说得轻一点让病人心态乐观,本来无可厚非,但须藤的这些处理,使得鲁迅对自己的病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精神,轻视病症,认为自己的身体即将痊愈,所以他在吐血、持续发热时还一直计划着去日本或者在国内疗养,热度未退就到处出门走动,最终因为受凉而导致病势爆发,最终去世。鲁迅几次大病都被误诊,由此可见,须藤的医术水平是很令人怀疑的,那么鲁迅为何一直如此信赖他呢?
一来须藤的沟通能力大概是很好的,鲁迅在9月5日评价他时说:“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与替鲁迅正确诊断了肺病的邓医生相比,鲁迅更喜欢须藤,认为他“也肯说明(有翻译者在),不像白色医生的说一句话之后就不开口”。二来须藤的收费比较便宜,根据陈祖恩的《上海日侨 社会 生活史(1868—1945)》资料,1902年,上海日本医会成立,统一规定上海日本医所的初复诊费、出诊费、手术费、药价、住院费。
其中出诊一次银3圆以上,再诊一次银2圆以上。皮下注射费是一次银0.5圆。但须藤为鲁迅诊治时,并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诊我的医生,大约第一次诊察费二元或三元以后一年内不要,药费每天不过五角,在洋医中,算是便宜的……”
须藤不要每次的再诊费2元,只收注射费,按照日记里他替鲁迅诊治的时间,光是1936年就替鲁迅起码省下了三四千大洋,相比较起来实在是非常便宜,须藤又极力宽慰病人,尤其是那句“再活十年,那时少爷也大了”可谓是说到鲁迅的心坎里去,黄源记得当时“先生听了也很高兴,立刻翻译给广平女士听”。
讳疾忌医是很多人的通病,鲁迅虽然没有忌医,但不喜欢说按照病症在5年前他就应该去世的美国医生,而喜欢说他的病都不致命、他还能再活10年、足够时间把稚子抚养长大的须藤,简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
鲁迅去世后,须藤在1936年11月《作家》杂志上刊登了《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表明自己的治疗是恰当、正确的,但此文与《鲁迅日记》中鲁迅自己的记载有较大出入,按照严家炎的判断,须藤有着编造病历,事后掩盖医师误诊和对疾病治疗的延误的嫌疑瑐瑡 ,这进一步让人对其的医术水平和医德人品有所怀疑,遇到这样一位医生,不得不说这也是鲁迅的不幸。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