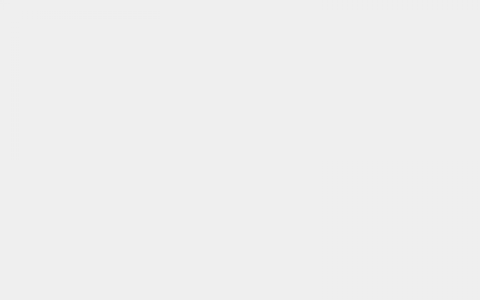因为从法学理论上讲,所谓的法律事实,就是客观事实。因为法律是有神明意义的。在法律面前,无所不知,无人可以蒙蔽它,更没有人可以规避它。
但是,一些无良的法官和法学理论家为了给自己的无能和无赖找借口,以所谓的法律事实为说辞,予取予夺,随意玷污社会公众的良知,以所谓的证据无法证明客观事实为由,随意虚拟所谓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法律事实,我个人认为这是社会的悲哀。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法律证据显示的事实和客观事实的确有很大的距离,怎么办,我们需要慢慢斟酌,剥茧抽丝,查明客观事实,不为一些表面的迹象或者证据所迷惑。这是法官的基本素养和智能。否则,都是无赖行径。
当越来越多的被法院查明的所谓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相违背的时候,我们的各级人民法院其实是在消费着自己的信誉和良知。
我和我的学生们为了解决目前人民法院无力更好地查明客观事实的弊端,曾经提出民诉法修改意见18条,直接发给了立法的起草者。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
如果大家乐意看到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无限的靠近,敬请关注我和我的学生谈睿、李明月、 李绍坤等人共同领衔起草的《民事诉讼法修改意见一二三》已经在今年的《现代商业》7月份期刊发表。在网络上搜索就可看到。
这个意见我们也计划编成小册子,《中华崛起十方略》,计划近期出版。
谢谢你对百度的关注。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
深信百度平台专家乐意为你 解疑答惑。
应该是优待战俘,主要是指日军在华被俘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吧战犯基本都被处理了,一个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了一批甲级战犯,而在中国国内的军事法庭则处理了一批乙级战犯
首先:优待战俘是一种国际惯例。二战期间,日本动用大量战俘作为劳动力,违反了优待俘虏这一国际规则,以至于后来日军无论攻击哪里,都遭到激烈抵抗,战争逐渐处于被动--倘若优待俘虏,对于战争时期劝降对手是很有帮助的,而虐待战俘,则只能让抵抗更加激烈,增加战争成本。即便是战争结束,对于战俘,如果虐俘,只会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进而使新中国外交变得困难重重。而优待俘虏,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新中国后来的国际外交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其次:这是和二战时有关--其实在整个二战中,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热衷于侵华战争,如左格尔案中的日本陆军军官中西功等,一批日本反战人士(包括日本共产党)其实是反对国家发动战争的,因此在二战中转而帮助盟军对抗日本军部。而二战中,一批被俘虏的日本中下级官兵其实并不想背井离乡发动侵略,在被俘后,经过改造,思想发生转变,在战争中,其实中国国共两党的部队里都有日本兵的身影(数量很少),这些人也为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牵线搭桥。
而除了这些人,还有一批,就是二战后被俘的日本战俘。他们被俘后,除了部分罪恶累累的战犯被审判处决外,大多数在受到优待和教育后,送回日本国内。而他们成为最早的一批中日友好人士。优待俘虏其实是为了日后外交做打算和铺垫。
其实,优待俘虏,是一种政治手段: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今日是敌,未必永远是敌,事实证明,后来这一行为对中日交流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冠通常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针对该情况,一般是没有必要囤药的。疫情期间备一点药是可以的。
其实不光是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平常可能自己家里面都要有一些OTC的药物,比如:感冒药、止咳药、治拉肚子的药,这些是最基础的药,那么可能还有些过敏的药,因为你到一个陌生环境里,这些基础的药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再去针对性的备一些药物,比如:变异性鼻炎的针对性药物,但是要特别注意到是OTC的药物。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比较强的病毒,能够以飞沫、气溶胶等物质为载体,在人与人之间广泛进行传播。在防治感染该病毒时,一般无需囤积药物。因为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并不建议患者立即用药,而是需要在出现症状后,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来针对性用药,并且要避免在同一时间内服用两种功效相同或相近的药物,以免药物成分对机体产生明显刺激,防止加重机体负担。在这样的治疗方式下,通常不需要提前准备大量的药物。此外,由于受到个人体质、病毒载量等因素的影响,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并非所有人都会出现完全一样的症状,这使得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药物也存在一定差异,而盲目囤积的药品可能并非针对这类症状的有效药物,无法在患病期间起到良好的作用。
因此,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时,可以适当地准备一些针对常见症状的药物,如有退热、缓解肌肉疼痛作用的布洛芬片、对乙酰氨基酚片、连花清瘟颗粒等,具有减轻咽痛功效的清咽滴丸、地喹氯铵含片等,但要避免过量储备药物。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