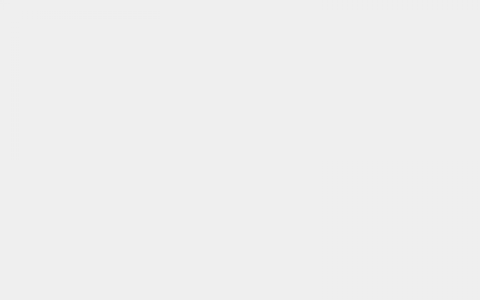那天,人生中第一次处死一个生命。
今早是实验课,有两个实验任务,一是血糖测试,二是1ml氯丙嗪对照实验,任务对象都是小兔子。
实验过程不多赘述,实在太手忙脚乱,但我忍不住想自夸一下自己还是表现的很镇静嘛,皮下注射和肌肉注射的进针很快没有犹豫~
上堂课为了之后的实验做铺垫,我们初次学习了耳缘静脉穿刺(兔子耳朵边的静脉注射),当时我们组穿刺的并不算顺利,想换一个耳朵穿刺,旁边有位学长说,不能用两只耳朵,如果两只耳朵都用了就只能处死它了。
所以这次实验我们也有意识的只使用兔子的一只耳朵进行血糖实验,可是很遗憾的是,老师还是告知我们处死它。
我们都很沮丧,老师便解释了处死的原因,圈养兔子的地下室十分脏乱潮湿,十分容易伤口感染,感染后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最终也只能处死。
老师特意强调,处死完毕必须行默哀礼。
我为另一只兔子肌肉注射完氯丙嗪后,它逐渐从活泼闹腾变得安静困倦,我不断的它的额头,看的它的眼皮逐渐合上。
它睡了。
而它的身后,被宣判处死的那只兔子,却瞪大着眼,眼珠子像是要突出来一样,无论如何拉下它的眼皮,它都不肯闭上双眼。
它死死的看着我们所有人。
我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第一次觉得死亡是如此轻易。
我以为我们是如何动手去弄死兔子,掐死?还是像生理课上的牛蛙一样捣碎脑子呢?
我是如此的害怕,然而处死一只兔子只需要20ml的空气罢了。
只需要20ml空气注入耳缘静脉,从挣扎到死亡不足一分钟。
空气进入血管那一瞬间,兔子的眼睛瞬间瞪出眼眶,死后无论如何拨弄都无法遮住眼睛。
我希望我永远记住此时此刻的敬畏与恐惧,那是对生命的敬畏——那双不瞑目的眼睛永远都在注视着我。
(二)
第三次气管插管手术实验,完全失败。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再次写到这件事时,内心已经没什么波澜了。
这次实验内容是气管插管,首先把兔子麻醉,切开脖子的皮肤,将气管剪成“⊥”型然后插管。
一开始麻醉就很不顺利,我特别害怕麻醉致死,就像老师说的,被麻醉到没有没有意识与痛觉时,正是游离在死亡边缘,所以组员推麻药时我一直惊呼着慢点慢点!
时刻检查兔子的各项神经反射是否进入深麻醉,每个兔子对于麻醉的敏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次手术兔子麻醉很不到位,三番几次兔子都醒了,可我仍不敢多推太多麻醉药。
好不容易总算能开始手术,主刀的是我,我爱使唤人,所以剪开皮肤进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剪开筋膜时特意避开了血管,所以血非常少。
直到气管暴露,那滑溜溜的,尚在波动的气管——
我瞬间害怕了。
这是气管,我怕我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兔子窒息而死。
我下意识的退缩让其他人继续手术,躲在一边看组员剪,换了好几次人才把气管剪开了一点,大家都是第一次手术。
于是不知是谁让别组已经做好手术的人过来帮忙,如果我知道后果…我怎么可能退缩
我以为我退缩了,就能有更优秀的人操作,可是没有,没有。
气道剪得十分不标准,几次插管都插不进,气道内不知为何开始渗血,血开始堵住气道,兔子拼命的开始呼吸,胸腔用力地起伏着,每一次呼吸都能听到气道里的水生——大家手忙脚乱地找老师,别组“成功过”的人仍然在插管。
我靠着墙,沉默地看了一会撇开头,我觉得我脑子空空的,漫无目的玩着手机,最终气道完全堵住,兔子宣判死亡。
当时我在便签里写:
“我犹豫不决我再三退缩我不果断我什么都想求助老师我不果敢我我轻信他人我没有及时阻止我不够细心”
我不果敢,剪开皮肤和筋膜我毫不畏惧,可当我准备剪气管时我就不敢下手了,我退缩。
我选择了退缩,结果“如我所愿”地兔子气管大出血窒息而死。
我一遍又一遍的反思,一遍又一遍的找原因,最终我找到了,气管切开术必须得把气管挑起来,将气管和气管筋膜分开,否则筋膜的血会渗进气管导致出血堵住气道。
可是又能怎样呢,兔子已经死了。
我的思绪再次回到实验室,冷冷的看着组员们毫不细心地行为,也冷冷的看着那个懦弱的自己。
我以为我退缩了就会有更好的人操作,这个实验能进行的更完美,结果都不过是半斤八两的水平,终究是错付了。
下一次,我绝不能再退缩!
(三)
这周的兔子实验不能说做的很完美,却也比上次好了很多,但我仍然陷入了反思,夜半难眠。
我大概明白了开这堂课的意义了。
一学期七次课能学到什么?技术吗?说实话,七次课都做不同的实验专题,其实练不了什么技术。我想,这堂课最重要的是培养思想,初次接触手术吧。
在课上,一次成功手术并不能代表什么,只能说比较聪慧,没成功也不能代表什么,未来真正上手术台必定是千百次的练习才能真正动刀,当下这堂课,更加应该悟到的是团队协作。
我们组已经不是第一次分工不明确了,遇到紧急情况也不懂的自我思考,连当下的兔子都无法冷静应对,未来真正的手术台上出现了突发的情况,也“找老师”?
还有组员那不必要的“共情”,手术是要操作规范,不是要小心翼翼,一点点发力就发出“嘶嘶”的疼音,实在让我不舒适。
有时候我也不禁好笑,下意识看向我做什么,我已经多次提醒该如何如何,没做好又何必来看我(当然被信任了我自然是开心)
还有剪开皮肤,分离筋膜,本该是主刀指导我与另一个副手夹起指定的筋膜,反倒全程是我指导了,我的视角是偏的自然会剪偏,另一个副手不懂变通,只夹着一处不动,不懂得与我协作,我不说我做的如何了,我只想说我们三个都是垃圾。
而且其他组员根本不参与实验,实验过程总有不够人手的时候,比如突发的情况大出血我和主要三个人员正在处理,难免顾不上麻醉,特别是固定在耳朵上的针管如果静止的话针管上的血就会凝固,堵住针管影响后边的一系列操作。
所以我思索了许久,下一次实验我大概不会参与主刀了。她们需要一定的独自思考,也需要有人掌控全局进行指导。
我做实验时是向兔子耳朵边缘的静脉注入10ml的空气,过十几秒兔子就会停止呼吸了,不过这种方法非专业人员很难做到,一般可采用楼上所说的断脊柱法。双毁髓法(破坏其脑髓和脊髓的方法)是用来处死两栖动物的。讲家兔置于解剖盘内,在同学的帮助下,将家兔固定,但不要用力过度,以免使家兔受伤,影响实验.然后抚平家兔的耳朵,在耳朵背面边缘处用酒精擦拭耳缘静脉,然后用注射器从耳缘静脉远端开始注射10ml空气左右,几分钟内家兔即死亡,家兔死亡之后,立即清洗注射用具,原处并还于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