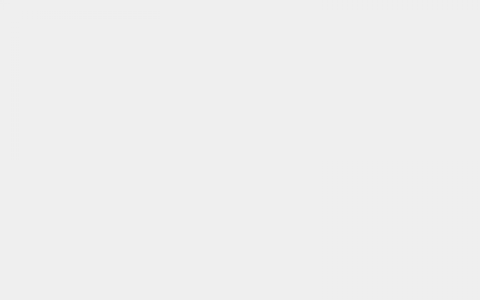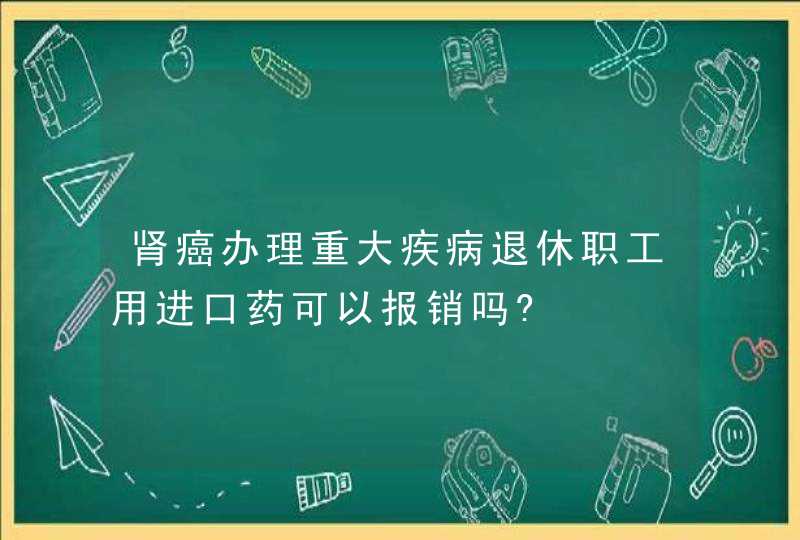
文:穷乡老叟
大暑的头天,母亲在我和大哥与大嫂的陪护下,终于从塞上榆林,回到了子州乡下的老家——四旗里。这对于母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尽管一路之上,母亲躺在车里的一副担架上,气息微弱,脸色煞白,呕吐不止,但从她被我和大哥抬得放在老家的土炕上后,发出的那一声低低的喟叹里,却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她如释重负后的那种坦然自在的心灵快慰。我想,母亲其所以会这么高兴,绝不仅仅是因为她感到自己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她觉得家乡有那些和她相处了一辈子的熟眉熟眼的乡亲,和她拼死拼活为我们弟兄奋斗了一生一世才修建起的那七八孔窑洞,以及为了生存,她曾在那山里川里,坡上洼下,没明没黑地挥汗留下的那些沉重的足迹。我知道,那其中实际包含了母亲太多、太多的不便于言说的人生 情感 和人格品味……
两年前的春季,母亲因患冠心病被我从老家接到榆林北方医院医治。住院一天后,一位面容姣好、慈善的年轻女大夫,忽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你母亲的肾可能有大问题。什么大问题?我紧张地望着那女大夫。我们怀疑是肾癌晚期。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的诊断一般不会出什么误差,但是为了确诊起见,你还是不妨带到西安或者北京的大医院再去检查一下,然后再考虑治疗的决定。肾癌?这、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我心里不由得就感到一阵痉挛似的疼痛。尽管那女大夫的语气很委婉、平和、人性,但我禁不住还是对她喊叫似的连连追问。然而,那女大夫再连什么话也没说,她只是以那种职业性的习惯同情,静静地望着我。少顷,我才觉得自己的失态,于是便急忙对人家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在脸上摸一把悄然流下的泪水,捂着剧痛的胃部,惶惶然走出了那女大夫的办公室。
那一刻,我很是急切的想看到母亲,很想抱紧母亲放声哭泣。可当我来到母亲的病房前时,却又丢了魂似的,无力推开那房门,不敢推开那房门。我怕我面对母亲时,会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就含着眼泪,在那病房前呆了很久很久。
我怎么也不相信母亲的命会这么苦,怎么也不相信母亲的生命会就此走到尽头。为了我们那个家,和往大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六七个,母亲受死受活地劳累了大半生,而眼见得现在的 社会 好了,光景日月好了,也该好好享受享受生活了,可母亲偏偏又……老天啊,你还长眼吗?我母亲在我的故里可是一个出了名的好人,一个德行感人的贤良女性啊。记得侄孙女玉莲很小的时候娘就去世了,孤苦伶仃的没人照看,没法儿生存。当时,母亲虽然拉扯着我们一大群孩子,少吃没喝的,那日子实在很难过,但母亲看着玉莲可怜,硬是叫玉莲吃住在我们家,硬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苦了自己,并一直将玉莲照看的长大成人,出嫁成家。爷爷晚年时病瘫在床,作为媳妇,母亲却不嫌脏,不嫌苦,不嫌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背出背里,接屎送尿,一直将老人家就那么地精心伺候到了老去。这是何等的不易,何等的难得啊。古往今来,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待老人,有谁能会如此贤孝?又有多少媳妇能够心甘情愿地做到这样?还有,还有……可好人为什么怎就得不到好报呢?我在暗暗诅咒老天不公不明的同时,痛苦地回想着母亲苦难而贤良的人生。
后来,后来我便不得不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本来这次接母亲出来看病,我仍不打算告诉任何亲人,还想就像以往那样,等母亲好转之后,再告诉大家,然后再让母亲到各处去走走,串串。可是……
我们将母亲哄骗到了省城。我们寄希望在对医学权威神灵似的敬仰崇拜中,得到母亲被地方医院误诊的命运裁决。
然而,在省城西京医院住院系统检查一周之后,我们所抱得那一点儿希望,还是彻底地破灭了。那里的专家教授什么的会诊后,最终还是告知我们说,你母亲患得是肾癌晚期。而且,还说癌细胞已经长进了动脉血管,根本就不能手术。假如硬要手术的话,恐怕连手术台上也下不来。多么残酷啊。
没法儿,最后我们只能痛苦地接受专家教授的建议,不对母亲化疗,只给她口服一种从德国引进的专门医治肝癌和肾癌的进口药。教授很是耐心地对我们推荐说,那药的中文名字叫多吉美,网上也可以查到,价钱看上去是有些贵,一粒就得好几百块钱,一般人是很难承受,但临床不久,却证明疗效的确不错,的确是目前世界上能够抑制肝、肾癌细胞扩散的最有效的药品。至于你们提到的化疗的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其实化疗是对患者的一种加速死亡,因为在每次的化疗过程中,在杀死那些癌细胞的同时,自然也会杀死患者那些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好细胞。这便是目前化疗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悲哀。所以,在决定保守治疗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们在经济上还可以承受的话,我们建议你们不要对你母亲化疗,不妨试试服用多吉美。再则,服用多吉美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只要患者服用够六盒15万元的药品之后,便可向中华慈善总会项目援助申请免费赠药。而只要申请批准了,之后患者无论服用多少药,也就再不用花一分钱了……真正是得病身无主。面对专家这样的苦口婆心,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虽然都是平凡小人物,都靠自己的清白、辛勤所得生存,生活并不富有,但为了母亲,就是再不富有,再承受不了,我们也要承受,也要搏一搏,否则,我们便愧为人子,将永远不得安心。
因此,在此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便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既要上班,又要外出奔波,苦苦为母亲买药和申请赠药。在单位,因为自己一时难免会对许多工作有所延误或缺位,我便不得不像一只狗一样的夹着尾巴做人;外出到医院、到慈善机构去申请办理赠药事务,又不得不像影视剧中的那些个毫无风骨的汉奸一般,变出各种笑脸,面对所有的冷眉冷眼,乖乖聆听那些个自以为圣洁、自以为高高在上者们的狗屁训导。但只要一想到是为了母亲,我就感到十分的坦然。
就这样,我们和母亲一起共同默默抗争着自己的命运。
至今,我们都严格封锁着消息,谁也没对母亲泄露她的半点病情,而母亲也从未问起过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但我们分明感到,打从到西安去住院检查时,母亲就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得的不是什么一般的疾病,而是那要命的恶病。她不说,不问,自然是我们兄弟姐妹求之不得的好事了,因为我们一直很怕母亲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从心理上产生恐惧,以致精神崩溃,加速死亡。所以,我们很希望这生命攸关的秘密,在我们之间,就这样心照不宣地直到那最后的一刻。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情,所以这两年多来,她躺在病床上老是嚷着要回老家,甚至一次次的对我们说,你们是不是就想看着我死到这里!这便使我们心里感到很是疼痛,很是为难。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一场,难道我们就连她的这点点要求也不能给予满足吗?这岂不是人们最最不齿的不孝吗?然而,我们清楚老家的条件,更清楚回去的结果。榆林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城市,别说是我们兄弟姐妹都在这里,护理关照都比较方便,而关键是这里毕竟有好多医院和医生,毕竟就医容易,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很快就能去医治。所以,我们就只好一次次地委屈母亲,劝说母亲,硬着头皮不让她回老家去,就盼望她的病情能有所转机,能多在世几天。
然而,母亲毕竟得的不是什么一般的疾病,而是那可怕的癌症。所以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每每在暗自庆幸母亲的生命竟是如此顽强的同时,总是又在那提心吊胆中,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曾经那么钢骨、那么要强的母亲,竟然在病魔和药物的摧残与折磨之下,一天天的日渐消瘦,日渐瘫痪在床,甚至连吃喝拉撒都再也不能自理了。而作为儿女的我们,在一边只能就那么干瞪着眼睛一任母亲在受罪,却就是没有一点儿办法去帮帮她,替替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磨难啊。我只好无奈地想,我们唯有能做的,就是在尽力医治的同时,尽量在母亲的人生末路上,多陪伴陪伴她,尽可能地让她老人家能够保持满足、保持尊严地离去。因此,今年我就只好向单位请了长假。我想,虽然我不配说什么“自古忠孝两难全”的官话,但我却知道,母亲我只有一个,我必须这么做。
老实说,我也早已是那两鬓斑白,为人之爷的人了,可对于母亲来说,我却永远只是一个儿子。我想,正像每个儿子小时候怎都离不开母亲的那样,当母亲疾病缠身,就要老去的时候,便亦离不开了儿子,亦像儿子小时候需要母亲的精心呵护的一样,需要儿子来对母亲细心照顾。对她问寒问暖,照料她吃喝起居,洗脸洗脚,还有接屎送尿什么的。我想,这类似轮回一般的苦乐人生,就是有关养儿防老的最基本的定义。也是人生一世,老来到头,最最切要的一个问题。
但单位就不同了。单位是由一些个毫不相干的人为了某一公众事业而组成的一个服务性群体,说实话,有谁也可以,没谁也可以。简言之,只要不是一个脑子里进水的,而确实是赋有一定的能力才智和公德意识的就行,那工作和那位子,就谁干都可以,谁坐都可以。试看 历史 上那些个曾经被人们敬如神明,捧为伟大,而他们自己也总以为自己很是神明、很是伟大的人物,在像常人一样死掉之后,地球不是照样转得很好吗?人们不是一代代的照样活得好好的吗?所以说,在单位谁也千万不敢把自己看得太重,更千万不敢不知道自己是谁,像那天王老子一般,利用人民——那些用汗水和心血养育自己的衣食父母——给予自己手中的那些权力,贪得无厌地见啥捞啥,见谁都想吃、敢吃,还每每要恬不知耻的在那大会小会上,不忘给自己的狗脸上贴金,欺世盗名地为自己头上戴上了一串串令人笑掉大牙的狗屁标签,妄自尊大,作威作福。须知,因果循环,凡事皆有报应。不报只是时辰未到罢了。
官人们面对功名,经常肯高谈阔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话。这其实没错,很好的,是古往今来每一个好男儿胸怀大志,放眼天下的人生理念,也是古往今来多少有识之士,为之穷其一生而追求奋斗的人生目标的最高极致,非常的感人。但世间多庸人。庸人的人生一般自然都是平淡无奇,却又实实在在。在公门中,一个人如能好好的顺心工作一辈子的话,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人生快事。如进而还能小有建树甚至亦能脱颖而出地加官进爵混出个品次来的话,更可值得称赞,值得庆贺。但你的小有建树和脱颖而出,是否像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一般不含有任何杂质?是否对于一个单位的好坏正邪与兴衰沉浮起到了一定的标杆作用?是否在那台上和台下、人前和背后,干的都是那襟怀坦荡能够见得了阳光的人事?我想,我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一个只懂得、只顾得偶尔给自己修修身而已的庸人,虽然在公门中领了纳税人几十年的血汗钱,但概未对他们干出一点儿可以看得见、摸的着的好事来。或许这就是我这个庸人和普天之下所有的庸人的可悲可恨之处。然而,对于母亲来说,我却是她眼前最最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我必须对母亲肩负起所有的责任和义务来。而就像人们都觉得自己的母亲是既平凡而又伟大的那样,我以为我母亲这一生真的不简单,她不但经历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而且更活出了令人敬佩的精彩。她的人生末路应该充满温暖充满爱,完全应该像那西下的夕阳一样,在我们做儿女的温情守护下、仰视下,绽放出那最后的异彩。我想,作为儿子,我必须这样,必须对母亲做到心怀感恩,念念不忘,必须尽力陪伴母亲欣然走完她有限的人生之路。
母亲最后的日子也许就要来了,她老人家病瘫在床上打着点滴,已有好久没有进食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痛苦地答应了母亲,做出决定——让母亲回老家。
尽管我们满怀忧伤地做好了一切不幸的准备,但我们仍期盼能有奇迹出现,好人能有个好报。果然,回家不几天,母亲的身体状况竟然慢慢地又有了好转,她又知道饿,知道要得吃饭了。而乡亲们也从刚开始的不明情况而不便前来探望,渐渐地也变得常来走动了。所以,母亲的心情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每当有人来看望她、来和她啦话时,她那憔悴而苍白的脸颊上,便会时不时地随着她的开心的笑声,露出一丝淡淡的红晕。
于是,我就想,我早该让母亲回家的……
久已未在老家多呆了,因此,对村里许多的人和事,甚至那些曾经十分熟悉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仿佛有些恍恍惚惚的生疏与淡忘了。但几天住下来,就像躺在炕上的母亲一样,我心里便也有了许多的踏实,许多的舒坦。
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乡亲来走串,来看望母亲。乡亲们都不是空手来的,有的拿着刚从地里采摘的葱嫩闪亮的新鲜青椒、芹菜什么的,有的则抱几个金子一般黄亮水嫩的玉米,或者提十几二十颗正宗的土鸡蛋。总之,全都是清一色的绿色食品,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礼轻仁义重,着实令人好生感动。
住在我家后面埝山渠的一位老嫂子,与母亲同庚,满脸皱纹,眼花耳背的,也是养育了儿女一大群的操劳命,也曾和母亲一样,遭遇过那可怕的饥饿折磨,经受过农业社那漫长而繁重的艰苦劳动。可是为了能多挣几个工分,叫生产队给自己评上个高分,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老嫂子和母亲一块扯峩、打夯、搬石头、挑大粪,什么样的苦活、累活都曾干过。老嫂子了解母亲,敬重母亲,知道母亲爱吃个家常便饭,爱吃玉米爱吃瓜,知道我们一大家子早就远离家门,什么样的农作物也不种了,所以她就不顾自己早年间落下的腰腿疼痛的毛病,不怕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上,几次抱着又甜又然的老云瓜,和玉米、蔬菜,专门给母亲送来。这实在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安和过意不去,因为我们深知为农的艰辛和不易。再则,又想我们并没有给老嫂子有过什么帮助。但这老嫂子却和所来的乡亲一样,对我们的不安报以爽朗的一笑,便说,这有什么,都是咱自产的嘛,等吃完了俺再给送来。哦,不不不!我连忙急着说,我们住这道高坡,你老嫂子这么大年纪了,腰腿又不方便,千万再不敢亲自送来了。嫂子想串、想和我妈啦话,就只管来。要是我妈还想吃的话,我来跟嫂子要就是了,嫂子看这样好吗?好好好!老嫂子见我这么说,就开心地笑着连声说好。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