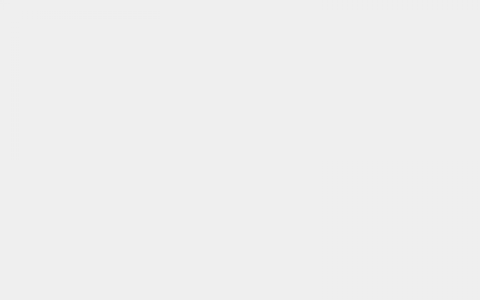我孩子上三年级,语文课文中就学到了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1937年12月,他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报名,并主动请求组建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
白求恩的祖父是医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主动拒绝特殊照顾。毛主席为白求恩写过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其中有“纯粹的人”这一评价。
1939年2月,率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
4个月里,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
7月初,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提议开苏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
与世长辞
11月11日早晨,在生命弥留之际,白求恩顽强地坐起来,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和翻译朗林分别写了一封长信。聂荣臻看后,当着众人的面不仅潸然泪下。
白求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加拿大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然而他也是由他的国家和当代世界所形成的。他真正是一个为那种要去体验和丰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驱策的新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物。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
你所不知道的诺尔曼白求恩
一、历史老照片
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几代中国人来说,经过历史潮流的若干次淘洗,白求恩就像是压在箱底的一只泛白的军挎包、一块旧表或一张老照片。历史的相片,有一张大家特别熟悉,那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1939年10月匆匆拍下的,后来被制成了邮票: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冬季大扫荡刚开始,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急行军70多里山路,在距火线5、6里远的一所小庙里搭起了临时手术台;白求恩身穿八路军土布军装和草鞋,正俯身在手术台前,身旁是几名助手;夕阳的光线从照片的左前方照进来,从侧面勾勒出他的白发、花镜、胡须、瘦削的脸颊和全神贯注的神情……。那时,距11月12日也就是他以身殉职的日子,已只有10几天了。
吴印咸的这张历史照片和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是我们几代人认识他的
主要依据: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老三篇”中的白求恩形象,也是被定于一尊的、高度抽象化的白求恩形象。当浓重的历史背景渐渐远退,这个形象也似乎变得空洞,成为一个道德偶像,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这个形象,我们现在就让它重新回到生活的真实中去。
二、一个放浪形骸的人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这一支白求恩族原是法国胡格诺派(法国新教)教徒,16世纪中叶迁居到苏格兰,18世纪移民到加拿大。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市的著名外科医生,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也是一名传教士。
白求恩从小就表现得有点胆大妄为,8岁的时候,他解剖苍蝇和牛腿,追到陡峭的悬崖边去捉蝴蝶,有一次摔断了腿。10岁的时候他一个人横渡佐治亚湾,差点儿溺死。他不但热爱科学和冒险,还喜欢用粘泥塑型,在画布上涂颜料。“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白求恩还在多伦多大学读医学。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参了军,被派到法国前线的战地救护队做担架员。后来,负伤,回国,重返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当了一名军医。
战争结束时,白求恩正在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服役。他和朋友们坐在巴黎的小酒馆里,那时,有些人梦想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原则“十四点”作为新世界的指南,有人尊奉费边社会主义,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解释世界,有些人在卡尔·马克思的旗帜下行动起来。白求恩发觉自己成了一个彷徨歧途、没有归宿的人。他感到幻灭,这是西方知识分子在战后二、三十年代普遍感到的幻灭。白求恩28岁了,两鬓未老先衰地生出了白发。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役。
他一面在医院做实习医生,一面到欧洲做商业旅行。他利用艺术鉴赏的本领,在法国和西班牙买进艺术品,然后在伦敦出售,赚了足够多的钱,使他能够过一种奢华的生活。他像贵胄子弟一样视金钱如粪土。他出手阔绰,买最好的服装、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还有无数的书籍,别人借钱则有求必应,他还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那时,年轻的白求恩走在街上,摆动着一根手杖,出入于伦敦放浪形骸的艺术家聚居的梭瑚区公寓。他性格直率,举止豪迈,为了内心的信念可以不计得失。每晚,年轻的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聚集在他的寓所,纵酒宴饮,听他高谈阔论他的艺术和人生观。他那时信奉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精神之父瓦特·佩特的学说,这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化英雄,倡导感官、兴味和快乐,所谓体验就是一切。在20年代早期的伦敦,白求恩就这样沉浸在浮华放浪的生活中,暂且疗治他的幻灭感。
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可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因为他遇到了两位女子。
三、中产阶级的名医
实习期满,他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埃丽诺·德尔夫人是这家诊所的主人,她极其富有,后来成了白求恩的朋友并资助他到欧洲深造。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大师们的手术,这使他终生受益。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遇到了弗朗西丝·彭尼。她22岁,是爱丁堡一户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英国上流社会女子学校给了她恬静脱俗的气质,这些加上她柔和悦耳的声音和美貌使他一见倾心。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婚后的白求恩偕妻子辗转欧洲和北美,最后定居在美国底特律城,那是新兴的汽车工业的都城。他开设私人诊所,很快就一举成名。但是,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俩相爱,但由于背景不同又彼此隔膜;他做事果决,但又性格急躁;他们的关系成了一连串争吵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循环。这一切即使在他们到了底特律以后也没有改善。可偏偏就在这时,他病倒了。
他得的是肺结核,这是改变他命运的疾病。他的两颊陷下去,头发更白了,眼睛烧得通红。他躺在床上,“我是完蛋了--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他用坚定的语气对弗朗西丝说,“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这是1926年。他在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里静养,与世隔绝,早年的荒唐经历恍如隔世,他已近中年,独自品尝着死亡的苦味。他说:“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已经厌倦了。在这以后无论什么也都没有意思了……”
绝望中,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得知有人正试验用外科疗法代替传统的疗养法医治肺结核。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得救。他深入研究后,要求在自己身上做手术。外科疗法的效果出人意料,他的咳嗽渐渐减轻,两个月后竟出院了。
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从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现在,他对底特律、私人开业和赚钱都没有了兴趣。他不再干普通外科,肺结核成了他唯一的兴趣所在。他和另外两位医生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压缩实验,成果发表在1930年的《细菌学学报》上,别的成果也由那些专业杂志陆续刊载;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新技术、新方法的设想,不断冒险在自己身上做各种试验,还发明了好几种胸外科器械,有的像肋骨剪,就是以“白求恩”命名的;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座大城市医院里行医,30年代已跻身于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的行列了。
白求恩挣很多钱,但是同早年一样总花得干干净净。他曾经和弗朗西丝复婚,一年后又再次分手。他继续做画、做雕刻,照顾当地的无名艺术家,总是出钱买他们的作品,还建了一所儿童美术学校。1935年秋季他在蒙特利尔举办了个人画展。那些年,他是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务界薪水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他是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上流社会追逐着他,但他与他们总是格格不入。
早年的幻灭感依然挥之不去。他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仅仅依靠胸外科疗法并不能治愈病人--那些贫穷的病人。他们越来越多,因为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已经持续几年了。
四、他是怎样向左转的?
几年前,也就是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出现波动,接着就发生了崩溃。失业、破产、贫困,银行、工厂、矿山纷纷倒闭,那些持“审慎乐观”态度的人士接二连三地从他们华尔街摩天楼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他注意到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悖谬:数百万人没有衣服穿,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忍饥挨饿,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有人讨5分钱想买杯咖啡,巴西却把咖啡倒进大海。
这种悖谬也侵入了他的医学领域,“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他说,“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世界历史正酝酿着战争和革命,他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
在蒙特利尔街头,他目睹了一次大规模示威。一队队骑警吹响警笛冲进人群,挥舞警棍四下乱打,男男女女纷纷倒在地上,因恐惧和疼痛而呼号。他从自己的敞篷车上取出药箱,为受伤的示威者包扎。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门突然打开, 一个衣着考究的人走进来。他递过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做……”他开始和穷人混在一起,到他们家里去,同他们一起开会,会见他们的领导人。这些人讨论哲学,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喜欢的温暖的同志之情接待他。
1935年,他作为加拿大医学界的代表到列宁格勒,参加那里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但其实他主要是想看看苏联“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看看“俄国人”。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获准参观了许多医院和疗养院,乘便做了调查。他发现,建国以后18年,尽管有近一半时间用于国内经济重建,但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却减少了50%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关于肺结核可以完全消灭的信念。在苏联,他发现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熟悉的西方世界正相反。在各个诊所和疗养院,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在这里,他一向鼓吹和设想的许多已经成为现实,比如针对儿童实行的结核病预防措施,比如针对肺结核患者采取的复原制度。
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回到加拿大后,便在全国做旅行讲演,用分娩和产痛作比喻,为俄国革命和苏联制度做辩护。他从医学专业的问题出发,却得出了社会的结论:保护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社会经济制度,消灭愚昧、贫困和失业。接下来是合乎逻辑的一步,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个传教士的儿子坚信,假如基督再生,这也会是他的选择。
那时,西班牙内战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选为队长。他辞去了圣心医院的职务,立下了遗嘱,三个星期后动身前往西班牙。
过去,肺结核是他的敌人;现在,法西斯主义是他的敌人。他组织了战地输血队,奔波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的前线,为伤员输血。佛朗哥的军队正步步逼近,到处都是血、断肢和尸体。经过西班牙内战,血与火把他淬炼成了一名战士。
白求恩回国了,在北美巡回演讲,为民主西班牙寻求更广泛的支持。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方,支援那里的游击队。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
五、最后一站:中国,太行山
接下来的故事是我们都熟悉的。他到了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他组织了战地医疗队,前往华北的抗日最前线--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
华北的父老乡亲正在与亚洲最强大的陆军作战,那些往日的庄稼汉、妇女、学生和军人们一起开会、训练、行军、唱歌,脸上泛着光芒。白求恩同他们在一起,发现了新的生活。他率领医疗队赶往距火线最近的地方,以他高超的医术抢救每一个伤员。有一次,他一连工作了40个小时,做了71个手术;另一次,他在69个小时里抢救了115个伤员。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他每到一地之前,他的故事就先开始传扬,而他的到来则使当地的士气为之一振,战士们常常喊着他的名字冲向敌人。
他49岁了,已满头白发,阅尽人生。艺术家/医生/游击队员,从早年放浪形骸的青年到中产阶级的名医,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和危机中合乎规律地左转,成为共产主义者。最终,他在亚洲大陆的腹地,在四分之一的人类中间赢得了尊敬和爱戴,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和真谛。如今回想起来,毛泽东的那段著名文字其实讲述的就是站在人生终点的白求恩: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