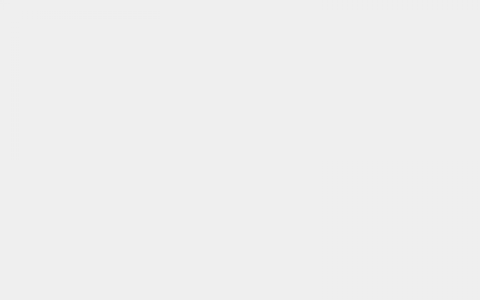村长铁青着脸,二话没说,先转过身去给我倒了一大碗酒,我郁闷地看看老金,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心想这什么情况啊,啥也不说上来就是一碗酒。难道这才是传说中的“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
我一想这事也是解释不清楚了,或许这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习俗吧,既然在人家的地盘,又借住在他家里,当然是入乡随俗了,于是也没多问,接过酒碗就要喝。
这时候突然感觉有人拧了一下我的后腰,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小声说,别喝。是老金的声音,我愣住转头看了他一眼,老金板着一张黑脸,悄悄冲我摇摇头。
我也不傻,当下就反应过来其中可能有什么猫腻。虽然不知道这猫腻具体是什么,但也留了个心眼,顺势把碗放下,打着哈哈跟村长解释道,“村长,这事儿还真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可话音一落,我就愣住了,这事儿还真不好说。玉香站在老金旁边,脸红得跟火烧云似的。我怎么说?难道跟她老子说,这事儿真不赖我,是你闺女主动跑来我房间勾引我的?
村长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眼神活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一样,我清了清嗓子,有些不自然,“咳...咳...,村长你也别误会,我和玉香姑娘就是在房里聊聊天,纯聊天,纯的不能再纯的那种......”
村长一脸你这个禽兽的表情,我朝玉香挤了挤眼,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帮我解释两句,她却全然没看见似的,站在原地低着头咬着嘴唇不说话。我一看这哪行啊,她这样子不是更说不清了嘛。
心想趁着村长脸色越来越难看之前,赶紧再找补两句,尽量解释清楚,顺便美化一下我在他心中的形象。组织了半天措辞,刚要开口,玉香却拉着村长径直往里屋去了,里屋不时冒出我听不懂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气很激烈,像是两人发生了什么争执。
若不是顾及着其他几个人可能会被我拖累,我巴不得现在就趁机撒丫子跑了。我悄声往老金身边挪了挪步子,心里盘算着要是这父女俩一会儿谈崩了,要是她爸克制不住要冲出来暴打我一顿,我往老金身后一躲,存活的几率应该要大一点。
果不其然,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狂吼过后,里屋安静了好一阵儿,我心里正犯怵,村长沉着一张比之前还要黑上几倍的脸走出来,直勾勾朝我走来,我心中大叫一声不好,赶紧往老金身后躲,村长看看老金,老金提小鸡一样把我提出来站到村长跟前。
我心中不断盘算着待会儿用什么姿势才能最大限度保护我这张脸不被打得太惨,村长突然伸出手,一把捉住我的手腕,他人虽然瘦,两只手却像铁钩子一样,抓得我动弹不得,我正要叫,他突然开了口,用蹩脚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愿,意,娶,玉,香,吗?”
我更是吓了一跳,有这么一个厉害的爹,即便玉香长得跟范冰冰一样我也不敢娶啊。况且前几天也听说了,这里的姑娘不外嫁,再喜欢也只能留在这里当女婿。这封门闭户的,我一大好青年哪里受得住啊。
我赶紧抓住村长解释,“村长,我跟玉香姑娘真没什么事儿,怎么能因为这一个莫须有的误会就耽误她一辈子呢?这样未免太对不住她了。况且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俩感情很好,来年就准备结婚了。”
这不算撒谎,当时我的确有一个相好的女朋友,只是脾气太暴躁。也就是两人互相消磨着时间玩玩,没想认真往下走,说不准哪天就散伙了。
村长还没什么反应,玉香听见我这话,哇地一声就奔回里屋哭了,我也不好意思进去劝,只得讪讪地站在原地。村长呆站了半天没说话,最后长叹了一口气,摆摆手示意我们回房休息吧。
我哪儿还敢回自己屋,赖着老金挤了一宿,说是随便眯俩小时,等天一亮立马收拾东西离开。
我基本没怎么阖眼,耳朵边尽是玉香呜呜的哭声,一夜未停,虽是也觉得一个漂亮姑娘哭成这样挺让人心疼的,可我能怎么办,总不能搭上自己的后半辈子吧,于是横了横心捂住耳朵不去多想。
天刚刚一亮,我就弹起来三下五除二收拾好东西拽着老金往外跑,把东西往车前盖上一扔,就回身去找其他人准备撤。赵胖子、小川睡眼惺忪地被我拽出来,没睡够一路嘟嘟囔囔,我来不及解释那么多,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这地方姑娘都敢半夜摸进房中,还有老金让我别喝的那碗酒,总是让我心里有一种毛毛的感觉,让我打从心底里对这个地方感到害怕、发毛。
这节骨眼上黑皮那小子却又找不着了,明明昨天半夜还在,怎么今天一早又不见人影了。车是他的,钥匙也在他那儿,没了他还真走不了。
我急得团团转,一刻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决定去找黑皮。这寨子小,周围除了树还是树,除了山还是山,枯燥无比,黑皮这么一个小青年能上心的,也就是那个玉腊了。
我辨了辨方向,拔腿就往玉腊家方向跑去,刚进寨子没两步,就见黑皮和那玉腊你侬我侬地依偎在树下。玉腊看黑皮的眼神和前几日完全不一样,尽是绵绵情意。黑皮也显得十分深情,正俯在姑娘耳边说着什么缠绵的情话,逗得姑娘耳根子一红掩嘴一笑。
我一看,嘿,这小年轻还真是精力旺盛,我只听说过赶集要赶早的,这天不亮就赶早谈恋爱的,这是头一次见。
也容不得多耽误时间了,我冲上前一把拉住黑皮就要走,黑皮一脸诧异,甩开我的手,“老王你干什么?!”说着重新将玉腊揽入怀中,两人看我的眼神活像是我是那棒打鸳鸯的恶人。
当着玉腊我不好明说,只得胡乱编了些瞎话,说什么临时有急事下山两天,拽着黑皮就要走。
黑皮和玉腊两人依依惜别,浓得化不开,我尴尬地站在一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玉腊泪汪汪地看着黑皮,黑皮说,你放心,没两日我就回来了。玉腊显然不放心,黑皮又安抚她,我什么时候对你食言过。
玉腊仔细想了想,认真点点头,毕竟还是小姑娘,看见我怪不好意思的,也就不再送黑皮,只招了招手在原地目送我们离去。
黑皮一路追着我问到底怎么了,我也顾不上答,赶紧催促着他把东西收拾收拾上了车再说。老金站在村长门口打了个招呼,不等村长出来便被我催促着上车踩上油门开车走了。
直到车子下山行驶出好远,我和老金才把头一晚的事情讲了出来。还没等说完,黑皮哈哈大笑起来,“老王啊老王,平时看着挺爷们儿的,怎么送上门来的艳福都不敢享,要是我早就拿下了。”
老金横了他一眼,一脚油门猛踩到底,车子轰地一声窜出去老远,才悠悠说道,“哼,我看那小丫头也是被你拿下了吧。”
黑皮向来怕老金,一时不敢接话,只在后头悄悄咧着嘴对我们笑笑,脸上不无遗憾,“可惜了可惜了,那么水灵的姑娘今天之后就见不着了。”
我不大看得上黑皮这种纨绔富家子弟的作风,他刚才讲的话也恶心,索性闭上眼睛补觉,不再理他,任由他低声向小川吹嘘着那玉腊身子的多多好处。
睡了没俩小时,黑皮又作起妖来了,直嚷嚷着没吃早点,又是血糖低又是血压低的,俩眼发黑,脑袋发晕。我心中冷笑一声,你小子就吹吧,就你这小身板,还享艳福呢。
受不住他哎哟哎哟跟驴似的叫唤,老金烦得没办法,只得将车调头,拐进临近的镇上买了些包子油条之类的招呼大家一起吃。 或许他真是血糖低,两个包子下肚,眼前清明起来,也不哼哼也不叫唤了,又活蹦乱跳起来。
我们略略歇了一会儿,重新出发,还没走出一百里地,这小子又叫唤起来,一会儿头疼一会儿背痒的。我们只当是这公子哥毛病犯了,谁也不愿搭理他。
但这小子叫唤得越来越厉害,由不得我们忽视了,老金赶紧将车靠边,我们一行人赶紧查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黑皮脸色青紫,嘴唇乌黑,整个人蜷缩在后排瑟瑟发抖,嘴里一会儿嘟囔着疼一会儿嘟囔着痒,问他哪儿痒,又说不上来,只说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痒,挠哪儿都痒,越挠越痒。
我们一合计,不好,这小子应该是突发什么病了,或者是吃了或摸了什么东西过敏了。于是重新上车杀奔最近的医院,老金把油门几乎踩到了底,一路按着喇叭狂飙,黑皮却更严重了,在后排上拼命喊着痒,伸手去死命地浑身乱挠,没过几分钟身上已经被他自己挠出一道道血痕了,皮肉翻开,红血直冒,看得人触目惊心。
我和小川赶紧伸手按住他,好在后座狭窄,没多大的空间,不然及我们俩小身板还真不一定按得住他。
双手被我们钳制住,黑皮痛苦地大吼,拿头砰砰撞着前排座椅,似乎撞得越疼他身上发痒的症状就能减轻些,黑皮死命地撞着座椅,丝毫不控制着力道,才三两下,头上便微微鼓起一片青紫。
我看看这黑皮不要命的癫狂样子,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小声说道,“这黑皮突然间就发了狂拉也拉不住,不会是他在嗑药吧。”
话音刚落几个人都不说话了,在云南边境毒品交易泛滥,究其根本也是因为有需求,尤其是边境地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我们纠结着还要不要把黑皮送进医院,一番讨论之后,还是决定杀奔医院。如果黑皮真的沾染上那东西了,趁早让他家里人知道,赶紧强制戒毒也好,否则这后半生就毁了。
到了医院,抽血、验尿各种检查一顿操作,忙了大半天,最后医生面色凝重地说一切指标都显示正常,他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自己挠出来的伤口有些深,要赶紧处理,否则容易发炎。
我当时就毛了,拍着桌子站起来,指着黑皮就对医生吼道,“这人都成这样了,你告诉我一切正常?你他妈会不会治,不会治就闭嘴找个有真本事的过来!”
医生讪讪一笑,“我们医院就属我资历最高,可能是因为我们医院设备不够先进吧,可能有些数据不那么准确,查不出来。建议你们把他转到大医院去,仔细查一查过敏源还有其他东西,或许能发现问题所在。”
“什么破医院,什么庸医,连病因都查不出来,还好意思腆着脸告诉我们一切正常。”我们骂骂咧咧架着黑皮往外跑,一口气不停地找到了景洪最好的医院,把人抬进去又是一顿检查,还是白折腾一场,所有检查都是正常,就是黑皮稍微有一点点脂肪肝,也不会导致他现在这种症状,少吃几顿好的也就慢慢缓过来了。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黑皮却眼见越来越虚弱,我们几个没了主意,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金却突然一拍脑袋,“噢,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